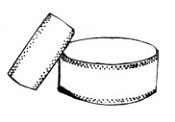钢琴家的魅力
导语: 老头端坐如钟,指头微微上翘,从钢琴上扭脸看看指挥朱利尼,一脸顽童相,调皮地浅浅一笑,继续埋头敲打莫扎特的第二十三协奏曲。真难为他,魔术师般诡谲的指尖儿伸缩挠拨,变出了那么多种音色!这是一张我偶然看到的影碟,从此就记住了霍洛维茨和善、好看的笑容。 少年时代,他可是我最崇拜的钢琴家。一闭上眼,往往见他在夜色里弹琴,手指跟琴键接触的地方迸出阵阵火花;或者,在烛影摇红的气氛里,我正默不作声,他那著名的“左手低音”突然自远处隆隆奔涌而来,不由分说地从外表安静的年轻人心坎上卷起热望和哀思。弹起斯卡拉蒂,他一路掉落精致的珍珠;他手下的舒伯特有种神秘的味道,前所未有地燃烧着天才的热情。他的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又华丽又悲凉,雄浑的意境里暗藏侠骨柔情,让人想起词中之苏、辛。在年轻人眼里,他有这么多让人疯魔的特质:大刀阔斧的阳刚气、浓厚而层次分明的色彩、卷舒自如的呼吸、几乎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怀、意兴所至的神来之笔……但随年龄增长,我又听到了鲁宾斯坦、施那贝尔、肯普夫、巴克豪斯这些权威,读了评论家们对霍洛维茨的严厉指责:他技巧很好,但喜欢炫技,个人色彩太重,太随意——无论弹谁的作品,
老头端坐如钟,指头微微上翘,从钢琴上扭脸看看指挥朱利尼,一脸顽童相,调皮地浅浅一笑,继续埋头敲打莫扎特的第二十三协奏曲。真难为他,魔术师般诡谲的指尖儿伸缩挠拨,变出了那么多种音色!这是一张我偶然看到的影碟,从此就记住了霍洛维茨和善、好看的笑容。
少年时代,他可是我最崇拜的钢琴家。一闭上眼,往往见他在夜色里弹琴,手指跟琴键接触的地方迸出阵阵火花;或者,在烛影摇红的气氛里,我正默不作声,他那著名的“左手低音”突然自远处隆隆奔涌而来,不由分说地从外表安静的年轻人心坎上卷起热望和哀思。弹起斯卡拉蒂,他一路掉落精致的珍珠;他手下的舒伯特有种神秘的味道,前所未有地燃烧着天才的热情。他的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又华丽又悲凉,雄浑的意境里暗藏侠骨柔情,让人想起词中之苏、辛。在年轻人眼里,他有这么多让人疯魔的特质:大刀阔斧的阳刚气、浓厚而层次分明的色彩、卷舒自如的呼吸、几乎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怀、意兴所至的神来之笔……但随年龄增长,我又听到了鲁宾斯坦、施那贝尔、肯普夫、巴克豪斯这些权威,读了评论家们对霍洛维茨的严厉指责:他技巧很好,但喜欢炫技,个人色彩太重,太随意——无论弹谁的作品,听上去都像他自己。同一数量级的大师里,数霍洛维茨招致的非议最多。这些评论有道理,可是,对霍洛维茨来说没什么意义——他知道自己的天赋和使命,知道该怎么去芜取菁地表达自己的激情——他是为这个才弹琴的。这些评论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霍洛维茨的琴声里不乏直接来自人性的朴素、犷野的冲动,闻者胸中自有热血,哪经得起这般呼唤!其他演奏大师常在让我惊佩的同时,隐约听到他们倾诉成功背后的艰辛,而霍洛维茨早已用更大的劳苦抹去了劳苦的痕迹,以更辛勤的雕饰超越了表面的繁华,打磨出了一个赤子充满情爱的世界。他在汪洋恣肆的琴声里朗声宣告弹琴是最大的快乐,音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假如你也曾有一番跟钢琴基本功“死缠烂打”的难忘经历,会觉出“快乐”的演奏是古典音乐世界里何等珍贵的天籁。
有两种人的演奏最令我感动,一种是霍洛维茨这样老到的大师,另一种就是琴童。印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的,是甜蜜的克列门蒂、讨厌的哈农,是去学琴的途中,在妈妈自行车的后衣架上多少回迎着狂风;是老师家天鹅绒琴罩上的美丽花边、映在琴键上的黄色阳光,是眼看小朋友们在窗外玩耍的气恼……童年的乐是至乐,苦是至苦,这强烈而单纯的苦乐与古典音乐的森严丛林浑然相融,早早地揭示了人生的多艰。看到那些可爱而稍显拘谨的男孩女孩们在台上弹琴,我时常百感交集。真难以想象,当年的霍洛维茨也曾如此。有传为证,他自幼用功。而以我所听所感,他仿佛用脊背牢牢顶住了身后那黑白相间的惨淡梦魇,留给人的是臂膀里色彩绚丽的广阔天地,任我们恣意去爱,去幻想。世上曾有霍洛维茨,我们没有理由不快乐。
钢琴家对我的魅力,是那种穿透理性,让人癫狂的巨大吸引。对任何东西爱了10年以上,都会有这种感情的。
不会又问我"最"喜欢哪个管风琴家吧。Walcha是好,但他只是森林中的一棵。管风琴家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管风琴录音受录音本身左右太大。我喜欢的录音中,相当多是比较新的,因为录得精准,声效好,但管风琴家的造诣是否一定超过Walcha,我也不敢说。
相关内容
- 如何避免练习钢琴时的不良习惯 2014-11-24
- 如何防止过度练习产生的伤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对摄像机你该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演奏文凭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9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8级教材目录2014-11-17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