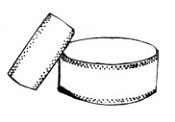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音乐畅谈】满族音乐发展的三大文化圈
导语: 在满族音乐(包括渤海乐、女真乐)发展历程中,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呈现出其生存、发展的三大文化圈,即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东北地区以满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满族人聚居地的满文化圈。 1.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 渤海国亡后,辽统治者唯恐其作乱,将渤海族人分散强迁至各地,到了金代,辽东地区的渤海族人逐渐增多,“人口达到五千余户,兵士有三万人”,金统治者也恐其难控制,故逐年将其迁徙到山东防卫,每年有数百户,“到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将渤海人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如此大批渤海人迁徙中原,必将渤海音乐文化带到中原,继续流传,最后以融入汉族音乐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隐性发展,正如《金史·乐志》载:“……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文化从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女真族都有较大影响。金统治者主张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汉人都是国人;主张学习汉语和汉儒的经书和理学等著作,拜汉儒为师(如金熙宗请宋人韩枋为师,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兄
在满族音乐(包括渤海乐、女真乐)发展历程中,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呈现出其生存、发展的三大文化圈,即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东北地区以满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满族人聚居地的满文化圈。
1.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
渤海国亡后,辽统治者唯恐其作乱,将渤海族人分散强迁至各地,到了金代,辽东地区的渤海族人逐渐增多,“人口达到五千余户,兵士有三万人”,金统治者也恐其难控制,故逐年将其迁徙到山东防卫,每年有数百户,“到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将渤海人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如此大批渤海人迁徙中原,必将渤海音乐文化带到中原,继续流传,最后以融入汉族音乐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隐性发展,正如《金史·乐志》载:“……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文化从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女真族都有较大影响。金统治者主张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汉人都是国人;主张学习汉语和汉儒的经书和理学等著作,拜汉儒为师(如金熙宗请宋人韩枋为师,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兄、子曾请汉儒张用直为师)。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的文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合本国语,制女直(女真)字”;宗教改信佛教和道教;其绘画、雕塑、建筑发展很快,皆似汉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医学等都有较大发展。在文学方面,女真文人在创作上跨越了汉文化的楚辞、汉赋阶段,“金一代的诗人,一开始就是从唐诗、宋词着手。女真文学的形式主要是诗、词、曲、散文、戏剧等。”金代兴起的“院本”和“杂剧”,为传入中原的女真族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其中“院本”运用了大量女真族音乐,据专家、学者考察:“在690本‘金院本’中,采用汉人古乐曲的只有16本,其余可能运用女真音乐或金代北方民族音乐。”此后,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元杂剧”和明代戏剧中,也明显地吸收运用了女真音乐。如元代著名女真族戏剧家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尤其是对女真人风俗和军俗的描写,具体而生动,演出时《虎头牌》采用了〈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女真乐曲。”《虎头牌》“剧本第二折用了许多源出于女真音乐的北曲,元明间这一折颇为流行,由于用17个曲牌组成套曲,通名‘十七换头’”。在元明间的戏剧中,贾仲明创作的《金安寿》和关汉卿创作的《南吕第一枝》的唱词中,曾提到的“者刺古”、“鹧鸪”、“垂手”都是女真族的乐舞名称,当女真音乐以其简约的民歌形态进入中原时,正值汉文化的戏剧发端时期,在此良机,女真族音乐从民歌跃入说唱和戏曲,进入了一个幸运的“时空”。以后又和其他北方民族音乐一起形成了日后较有影响的“北曲”。《中国音乐词典》“北曲”词条云:“(北曲)其中有唐、宋以来的歌舞大曲,宋、金以来的说唱诸宫调,宋代流行的词调,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等说唱音乐或歌舞音乐,还有少数民族的民歌,尤其女真族的民歌占有相当比重。”另外,女真族的“臻篷篷歌”和太平鼓也传入中原,“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至明朝“京师有太平鼓之戏”,而且“有结为太平鼓会者,聚众数百人。”
清入关后,统治者一方面为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积极竭力学习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为维护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意识又制定了一些方针措施。由此,形成满文化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又逐渐融入汉文化的历程,在此历程中“八旗子弟乐”的出现,以及“八旗子弟乐”中的子弟书、牌子曲、高跷、太平鼓、和经过“八旗子弟乐”化的什不闲、太平歌、道情等音乐与其后中原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东北的东北大鼓、二人转等音乐的渊源关系、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满文化特征。正如李家林在《关于〈北平俗曲略〉的话》一文的第一部分“北平俗曲的来源”中所说:“我们研究北平俗曲的结果,知道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从外省输入的。……东北由辽金清输入打连厢、倒喇、群曲、蹦蹦戏等;……传播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诸族为主,……”
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将满族诸部编成八旗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由此满族的民间音乐也被带到全国各地,流传在驻守边疆八旗军中的“八旗子弟乐”,便是在满族民歌和萨满神歌的曲调上,填以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词,用八角鼓伴奏,来抒发心中思乡之情的音乐。这种长于抒情、叙事一唱到底的音乐形式传入京都后,受到人们喜爱,八旗文人便参照民间鼓曲的格式和北方音韵的“十三道大辙”,创作出近似鼓曲的“八旗子弟书”,后因初创地域和风格不同,又分成“高亢红火、慷慨激昂”的“东城调”和“缠绵悱恻、婉转低回”的“西城调”。最初“八旗子弟书”用满语写作演唱,在逐渐混入汉语演唱时称为“满汉兼”;其后根据听众的需要,又有一部分满汉文对照的唱本,或用满语或用汉语演唱,谓之“满汉和壁”;最后因满族通用汉语,故“子弟书”也都用汉语写作和演唱了。在此期间,“子弟书”传到天津,形成“语言通俗流畅,接近方言口语,节奏较快”的“天津子弟书”(也称“卫子弟”);后又传到盛京(沈阳)称为“清音子弟书”。清末。“子弟书”衰落。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流行于京津一带的“梅花大鼓”,以及与“木板大鼓”相结合的“京韵大鼓”。
在东北满族人民中,还流传着一种手执八角鼓自编自唱的艺术形式,名为“八角鼓”。清入关后,它已具有说唱特征雏形,也传入关内。此后,“八角鼓”的表演形式以满文化特征和其他满族音乐文化因素,以及中原音乐文化一起促成“单弦牌子曲”的形成和发展。“单弦牌子曲”运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其音乐吸收“子弟书”中的“西城调” 和明、清流行的时调小曲(其中有可能包括满族民歌和满族八角鼓音乐),以及因满族士兵宝恒(又名小岔)唱得最好而命名的“岔曲”。在其表演形式从群唱改变成“单弦”形式,以及文学、音乐内容又进一步充实提高时,满族单弦表演艺术家德寿山等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满汉文化,此后,“单弦牌子曲”盛传不衰至今。此外,满族八角鼓也对其他地区的说唱艺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山东流行的聊城八角鼓与满族八角鼓有渊源关系,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都吸收过八角鼓的曲牌。”
上述表明,满族及其先世的音乐在进入中原后,伴随着汉族音乐的进化,也处在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它在不断发展中与汉族音乐相融合。事实证明,北方中原的民间音乐的旋律舒展流畅、节奏清晰欢快、性格阳刚爽直等特点的形成,无不受着北方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其中也包括满族音乐文化)的影响。
相关内容
- 如何避免练习钢琴时的不良习惯 2014-11-24
- 如何防止过度练习产生的伤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对摄像机你该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演奏文凭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9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8级教材目录2014-11-17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