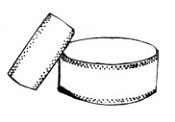印象派的继承大师:拉威尔(二)
导语: 相关链接:拉威尔《波莱罗舞曲》 拉威尔《鹅妈妈》组曲 1875年3月7日,杰出的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出生在比利牛斯山谷靠边境的一个小城西布恩。父亲是个有瑞士血统的法国工程师,曾应聘去西班牙搞铁路建设,在那里认 识了一位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姑娘马丽·德劳特,他们结成夫妇。小拉威尔出生才几个月,全家迁往巴黎。三年后,添了弟弟爱德华。父亲爱好音乐,想培养两个儿子成音乐家,结果只有莫里斯走上了这条通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波及到这位音乐家,他入伍当兵,在军中任货车驾驶员。战争对他是一场可怕的经历,他逐渐对 帝国主义的嗜杀深恶痛绝,感到德、法两国人民卷入这场战 争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不顾舆论的指责,拒绝签名支持一个旨在阻止法国演出德国音乐的组织。1917年他的母亲去世, 更使他陷入了严重的沮丧之中,健康急剧恶化,于这年夏天退役。
大战对他的影响在停战后还久不消失,他失眠,不时情 绪低落,写得很少。悼念战死友人的《库泊兰之墓》,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为换一下环境,恨作精神,他移居乡下, 动手写作几年前狄亚吉列夫委托他写的芭蕾音乐《大圆舞曲》。作品完成并在音乐会上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后,狄亚吉列夫却认为它不适合演出而加以拒绝。拉威尔大为恼怒,两 人从此绝交。此时,他还将许多时间用于旅行演出,几乎访问了欧美各国,指挥演出门已的作品。后在离巴黎不远的风景如画的蒙伏拉莫瑞村找到一所小别墅,在那里专心作曲, 过着恬静平淡的生活。创作了轻歌剧─芭蕾《孩子与魔法》、《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曲《茨冈狂想曲》、《波莱罗》及两部钢琴协奏曲。
1932年他遭到一场车祸,头部受伤。不久,出现了偏瘫的征兆。曾尝试休假治疗,前往西班牙、摩洛哥旅行,仍无显著好转,自此丧失了工作能力。1937年12月19日做脑手术无效,于28日凌晨在医院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拉威尔的生活与创作处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对艺术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现代作曲家’,因为我的音乐远不是一场 ‘革命’,而只是一种‘进化’。虽然我对音乐中的新思潮一向是虚怀若谷、乐于接受的(我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中就有一个勃鲁斯乐章),但我从未企图摒弃已为人们公认的和声 作曲规则。相反,我经常广泛地从一些大师身上吸取灵感 (我从未中止过对莫扎特的研究),我的音乐大部分建立在过 去时代的传统上,并且是它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我可不是一 个擅长于写那种过激的和声与乱七八糟的对位的‘现代作曲 家’,因为我从来不是任何一种作曲风格的奴隶。我也从未与 任何特定的乐派结盟。”
他重视旋律的作用,曾对他的学生──著名的英国作曲家沃恩·威廉斯说过:“在一切有生命的音乐中,都有一个含蓄的旋律轮廓”。他运用的调式及和声都新颖别致,常用自然调式、五声音阶及不解决的七和弦、九和弦等,但总是以传统和声为基础,从不在无调性的领域里走得太远。他所运用的节奏则有不少受舞曲的制约。他偏爱舞曲体裁,如法 的小步舞、帕凡、里戈顿,西班牙的马拉加尼亚、哈巴涅拉、波莱洛等,拉威尔将这些舞曲处理得典雅情致、明晰优美,具有法国音乐的特点。拉威尔是位公认的管弦乐大师,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管弦乐配器的方法,充分发挥每个乐器的表现性能,形成异常精美与华丽多彩的效果。他的作品结构明确,织体清晰,总的风格倾向于古典音乐的纯净优美和富于幽默感。而拉威尔最重要的创作特征是对技术的尽善尽美的追求,尽管他技术高超,但对待每一部作品仍然是反复推敲、精心雕琢,不到极端完美决不罢休。他曾对他的传记作者马纽埃尔说:“我的目标是技术完美,因为我确知这一目标永远无法达到,所以我要求自己不断向它靠近。”因拉威尔这一癖好,斯特拉文斯基曾戏谑地地称他是位“精巧的瑞士钟表匠。”
拉威尔还是个优秀的教师,但仅教几个他感兴趣的私人学生。在他自己学习时期,经常以马斯奈(法国作曲家,1842一1912)的话“为了掌握自己的技术,必须研究别人的技术”作为格言;当他教授学生时,常常给青年作曲家的一个 劝告是:“找个蓝本来临摹。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说的话,最好还是临摹。等到体有话要说时,你自然不会照抄的,那时,你的个性会最明显地呈现出来。”他也写过少量的但很有特点的文章,对同时代作曲家的作品总是充分肯定;对有才华的青年人更是积极支持。
总的来说,拉威尔的生活圈子狭小,艺术天地有很大的 局限。综观其作品,题材比较狭窄,作品的内容很少直接源自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多是对景物的描绘和表现童话、传说 故事等,音乐中缺乏对生活的炽热的感情。这反映了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状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脱离社会现实的心理状态。 在早期,拉威尔的音乐受到印象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他逐渐摆脱了印象主义的美学思想的约束,写出了一些形象清晰、生动,色调明朗,在艺术上有许多创造 并给后人以启迪和影响的作品。他的音乐,是以法国的音乐文化为基础的,而在充分发挥管弦乐的色彩特点上,他有着 许多的创新。因此,拉威尔在法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