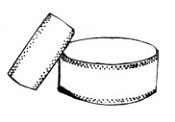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胡琴皇后”宋飞精通13种民族乐器(一)
导语: 精通胡琴、古琴、琵琶等13种弦乐器的国乐大家宋飞,曾先后在天津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师从于宋国生(其父)、安如砺、刘明源、陈重、李祥霆、王范地、张子谦等众多民族音乐教育家、音乐家,在业界有“二胡皇后”、“胡琴皇后”甚至“民乐皇后”的美誉。1998年和1999年春节,宋飞曾随中国民族乐团两次献艺维也纳金色大厅,受到西方观众的热情追捧;2002年,她在北京举办了《弦索十三弄》个人独奏音乐会,在音乐会上一人演奏了二胡、高 胡、古琴、琵琶等13种乐器,在音乐界引起极大反响。2006年,宋飞在取材于张择端传世名画、并由作曲家史志友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领奏了二胡、坠胡、高胡、中胡、板胡、二弦、京胡等7种胡琴,被媒体称为“国宝级音乐大典”。 文/本报记者苏蕾 回归传统民乐大家的研修方式 广州日报:您精通各种胡琴、古琴、琵琶等13种民族乐器,是如何掌握这么多乐器的? 宋飞:与以往民族音乐的传承不同,这个时代的音乐分工很细,也在试唱练耳等方面和西方接轨,

精通胡琴、古琴、琵琶等13种弦乐器的国乐大家宋飞,曾先后在天津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师从于宋国生(其父)、安如砺、刘明源、陈重、李祥霆、王范地、张子谦等众多民族音乐教育家、音乐家,在业界有“二胡皇后”、“胡琴皇后”甚至“民乐皇后”的美誉。1998年和1999年春节,宋飞曾随中国民族乐团两次献艺维也纳金色大厅,受到西方观众的热情追捧;2002年,她在北京举办了《弦索十三弄》个人独奏音乐会,在音乐会上一人演奏了二胡、高 胡、古琴、琵琶等13种乐器,在音乐界引起极大反响。2006年,宋飞在取材于张择端传世名画、并由作曲家史志友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领奏了二胡、坠胡、高胡、中胡、板胡、二弦、京胡等7种胡琴,被媒体称为“国宝级音乐大典”。
文/本报记者苏蕾
回归传统民乐大家的研修方式
广州日报:您精通各种胡琴、古琴、琵琶等13种民族乐器,是如何掌握这么多乐器的?
宋飞:与以往民族音乐的传承不同,这个时代的音乐分工很细,也在试唱练耳等方面和西方接轨,却鲜出过去那样的大师。
我要回归过去那些民乐大师的行为轨迹和研修方式——除了二胡,阿炳还精通琵琶和笛子,刘天华更是学贯中西,他会小提琴、小号、琵琶等等。我一直很喜欢琵琶,但上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父亲觉得弹琵琶的人太多,就让我学古琴。上大学的时候,我修了二胡和古琴双主科。到了大三,因为还是喜欢琵琶,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毕业之后,我又开始学京胡、坠胡。“弦索十三弄”可以说是我回归传统民乐研修方式实践成果的发表。
广州日报:同时学这么多乐器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吗?
宋飞:我不可能付出13个人的时间和体力、精力、脑力,但我从小就不是单一轨迹,所以倒不觉得有负担。我往往是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和追求来带动 技术的成长,我学不同乐器的目的,是为了让二胡演奏能对民间传统的东西表达更到位,因为很多作品都需要方言化的表达。例如,坠胡让我加深了对河南音乐的了解,于是用二胡拉河南小曲时我就借鉴了坠胡的特点。
同时,我学习时采用的是非常规方式,将各种乐器分类,对它们进行比较式把握,只记每个乐器与其他乐器不同的东西。其实,每种乐器都并不特别 难,最难在于“弦索十三弄”更换曲目时要在不同乐器之间来回转换,因为每种乐器的定弦、指法等都不同,这场音乐会要求演奏者对各种乐器了如指掌、驾轻就 熟,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能在头脑中迅速进行信号转换。
拉二胡双手的配合就像打太极
广州日报:您掌握的这13种民族乐器大致可分拉弦和弹拨两大类,它们各自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有没有可以触类旁通的?
宋飞:拉弦乐器讲究定弦、把位大小、右手运弓力度和方式、左手指距和指序等;而弹拨乐器,我更多是通过内心的歌唱和对音乐性的追求,去弥补技 术上的不足。至于触类旁通,肯定是有的,例如我用二胡演奏《大浪淘沙》时,注入弦乐的歌唱性,还模仿了琵琶的演奏手法,给听者以“弹出来”的感觉。类似这样超常规演奏技巧和方式的例子还有不少,这让我音乐的路子变宽。
广州日报:有些人认为,会拉小提琴的人,二胡就不在话下,您认同吗?二胡的弓法有什么特别讲究?
宋飞:西方小提琴有二胡值得借鉴的技巧,我们也出过《梁祝》这样小提琴民族化的精品,但小提琴和二胡毕竟是两种乐器,技巧完全不同,二胡没有 指板,弦与琴杆之间是悬空的,下指的量感很丰富,表达音乐的分寸也就非常丰富。其实,二胡的微妙处也正在于它这种悬空所带来的丰富表现力,可以利用滑音、揉弦、装饰音等等来表达情感。中国音乐语言讲求虚实动静,我学那么多乐器,也是为了把握其这一特色。
二胡的弓法就像中国书法,有顿、提、折等各种手法的丰富呈现。不仅各种音色都要由运弓来实现,而且运弓蕴涵了很多学问,演奏二胡时双手的配合,就像打太极,是很玄妙的。
广州日报:您作为目前国内二胡的顶级演奏家,和其他演奏家相比有什么“杀手锏”?网上有很多关于您代表作的探讨,您自己怎么看?
宋飞:我从不为自己设定代表作,我在演奏上“不挑食”,只要是我喜欢的,都会把它变成自己的。而我真要说有一个“杀手锏”,应该就是我永远在变,包括弓法、指法,就像狂草,没有固定的写法,情境到了自然一气呵成。
曾三年不练曲“极端”突破瓶颈
广州日报:大家都说您善于吸取古典的、民间的、西洋的音乐营养,您在这方面有何体会?
宋飞:音乐需要开放和传承。我和大家一样,在什么都不会的时候,经历了书法临帖,即规范训练的阶段,不少演奏家都曾是我模仿的范本;但没有技 巧不行,而过于强调技巧又会成为音乐表达的障碍,而所谓大师,就是到一定时候打破规范、追求个性,继而形成自己独创的方式。我从小就听阿炳的录音,可以准 确模仿他的《二泉映月》,同时我也留心其他前辈演奏家怎么拉这首曲子,在模仿、比较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拉。不能总是停留在模仿的阶段,最终要消化成 自己的东西。
广州日报: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又如何克服的?
宋飞:我曾和父亲探讨演奏家的境界,比顶天立地更上一层,是惊天地、动山河,再往上呢,应该就是无须表达,别人已能自然感受到。拿古琴来说, 我曾经音准、技巧都没问题,但总感觉弹出来什么都不是,而我的老师当时91岁了,手脚不灵,音有时也不准,但他往那一坐就比我强,气韵就是了。所以,我在 1999年之前的3年,曾用过一个很极端的方法,就是天天只拉音阶、不较劲去练作品,仅仅在头脑中熟悉音乐,希望能让技术变成鲜活的、自如的、下意识中就 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这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和冒险,不成功就是退步,结果,1999年我录第一批教材时,《葡萄熟了》和别人及自己以往的都不同了,我知道自己越过了一个台阶。
广州日报:您现在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是演奏和教学“两条腿走路”的,您教学生最注重的是什么?
宋飞:中国民乐博大精深,有各种风格、流派,学习者需要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不断累积演奏技巧,我主要是让学生找到与音乐沟通顺畅的方式。同 时,我推行的理念是“健康演奏”,即心理、生理和乐器物理都要健康。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需要自然坦诚的表达,如果你紧张、心跳加速,动作就会僵化、不 自如,而乐器的声音表现也自然不健康。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