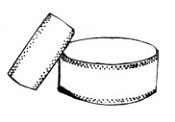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音乐杂谈】作品选读:我与音乐
导语: 音乐,从字面上,大约可以理解为声音的快乐,或声音带给人的快乐。从名词的角度理解,就要复杂得多,几句话说不清楚。 我想,最原始的音乐大概是人用自己的器官来模拟大自然里的声音。譬如要抓野兽,就模拟野兽的叫声;不但引来了野兽,而且很好听,于是,不断重复,并且学给同伴们听,这就既有创作,又有表演了。不抓野兽时,要召唤远处的同类,便仰起头、发出悠长的吼叫。有的吼得好听,有的吼得不好听。吼得好听的就是歌唱家。让人快乐的声音就是最早的音乐。渐渐的,单用器官发出的声音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树叶、竹筒或是其他东西来帮助发音。这些东西就是最早的乐器。 我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骑在牛背上,一阵寂寞袭来,突然听到头顶上的鸟儿叫得很好听,叫得很凄凉。不由抬头看天,天像海一样蓝。我那颗少年之心,也变得很细腻、很委婉,有一点像针尖儿,还有一点像蚕丝。我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在心中涌动,时而如一群鱼,摇摇摆摆地游过来了,时而又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好听的声音,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欢乐。音乐实际上是要唤起人心中的情——柔情、痴情、或是激情……
音乐,从字面上,大约可以理解为声音的快乐,或声音带给人的快乐。从名词的角度理解,就要复杂得多,几句话说不清楚。
我想,最原始的音乐大概是人用自己的器官来模拟大自然里的声音。譬如要抓野兽,就模拟野兽的叫声;不但引来了野兽,而且很好听,于是,不断重复,并且学给同伴们听,这就既有创作,又有表演了。不抓野兽时,要召唤远处的同类,便仰起头、发出悠长的吼叫。有的吼得好听,有的吼得不好听。吼得好听的就是歌唱家。让人快乐的声音就是最早的音乐。渐渐的,单用器官发出的声音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树叶、竹筒或是其他东西来帮助发音。这些东西就是最早的乐器。
我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骑在牛背上,一阵寂寞袭来,突然听到头顶上的鸟儿叫得很好听,叫得很凄凉。不由抬头看天,天像海一样蓝。我那颗少年之心,也变得很细腻、很委婉,有一点像针尖儿,还有一点像蚕丝。我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在心中涌动,时而如一群鱼,摇摇摆摆地游过来了,时而又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好听的声音,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欢乐。音乐实际上是要唤起人心中的情——柔情、痴情、或是激情……
1977年初,我在黄县当兵,跟着教导员骑车从团部回我们单位。时已黄昏,遍地都是残雪泥泞。无声无息,只有自行车轮胎碾压积雪的声音。突然,团部的大喇叭里放起了《洪湖赤卫队》的著名唱段: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人们都停下了车子,侧耳倾听。我感到周身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围了。
歌声把我拉回了童年。“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童年炎热的夏天,在故乡的荒草甸子里,在牛背上,听到蚂蚱扇动着翅膀,听到太阳的光芒晒得大地开裂。用葱管到井里去吸水喝,井里的青蛙闪电般地沉到水底。喝足了水,用葱管吹出潮湿流畅的声音,这就是音乐了。
我们村子里有一些大字不识的人,能拉很流畅的胡琴,他们嘴里会哼什么手里就能拉出什么。他们闭着眼,一边拉一边吧嗒嘴,好像吃着美味食品。我也学过拉胡琴,也学着村中琴师的样子,闭着眼,吧嗒着嘴,好像吃着美味食品。
母亲说:“孩子,歇会儿吧,不用碾小米啦,今天够吃了。”我说:“这不是碾小米,这叫摸弦。”因为不懂简谱,更不懂五线谱,全靠摸。那些吧嗒嘴的毛病,就是硬给憋出来的。等到我摸出《东方红》的曲调时,就把胡琴弄坏了。想修又没钱,我的学琴历史到此结束。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盲人来村中演唱。有一个皮肤很白的年轻盲人能拉一手十分动听的二胡,村中一位喜欢音乐的大姑娘竟然跟着他跑了。那姑娘名叫翠桥,是村中的“茶壶盖子”,最漂亮的人。最漂亮的姑娘竟然被盲人给勾引去了,这是村里青年的耻辱。从此后,我们村掀起了一个学拉二胡的热潮,但真正学出来的也就是一半个,而且水平远不及那盲人。可见,光有热情还不够,还要有天才。
我家邻居有几个小丫头,天生是音乐奇才,无论多么曲折的歌曲,她们听上一遍就能跟着唱。听上两遍,就能唱得很熟了。她们不满足于跟着原调唱,而是一边唱一边改造。她们让曲调忽高忽低,忽粗忽细,拐一个弯,调一个圈,勾勾弯弯不断头,像原来的曲调又不太像原来的曲调。我想,这大概就是作曲了吧?可惜,这几个女孩的父母都是哑巴,家里又穷。几个天才,就这样给耽误了。
忽然听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很入了一阵迷。这曲子缠绵悱恻,令人想入非非。后来又听到了贝多芬、莫扎特什么的,听不懂所谓的结构,只能听出一些用语言难以说清的东西。一会儿好像宁死不屈,一会儿又好像跟命运搏斗。这大概就是音乐形象吧?谁知道呢!
我听音乐并不上瘾,听也行,不听也行。对音乐也没有选择,京剧也听,交响乐也听。有一段,我曾戴着耳机子写字,写到入神时,就把音乐给忘了。只感到有一种力量催着笔在走,十分连贯,像扯着一根不断头的线。
我看过一本前苏联的小说,好像叫《真正的人》吧。那里边有一个飞行员试飞回来,兴奋地说:“好极了,妙极了,简直就是一把小提琴!”我快速写作时,有时也能产生一种演奏某种乐器的感觉。经常在音乐声中用手指敲击桌面,没有桌面就敲击空气。好像耳朵里听到的就是我的手指敲出来的声音。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却享受到了音乐带给我的快乐。快乐在这里是共鸣、宣泄的同义词。大概,绝大多数音乐不是供人欢笑的。如果有让人欢笑的音乐,那也是比较肤浅的。
我基本上知道,艺术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但非要说出来是不可能的。不说出来,但能让人感受到,这就是音乐,也就是艺术。
(选自《河北日报》)
相关内容
- 如何避免练习钢琴时的不良习惯 2014-11-24
- 如何防止过度练习产生的伤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对摄像机你该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演奏文凭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9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8级教材目录2014-11-17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