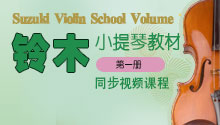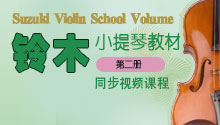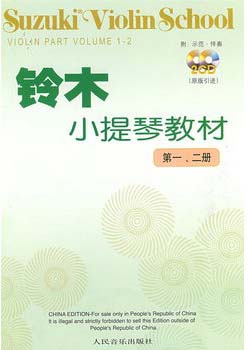俞丽拿:一曲《梁祝》伴随一生(二)
导语: 一曲《梁祝》,绕梁47年。当年短发、蓝裙,就像蝴蝶般从弦上轻盈起飞的首演者俞丽拿,转眼已花甲。今晚,俞丽拿将携此曲首登河南省人民会堂。她事先并不知道,上个月,河南汝南的“梁祝传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场演出,也就相当于在祝英台的“家门口”演奏。 演出前记者造访,俞丽拿平静如常:“不论在哪里演奏《梁祝》,都是一样的情怀,祝英台在我的心里。”说罢,忽然来了兴致,操琴开弓:恍惚之间,彩蝶仿佛从她的弦上飞出,《梁祝》之美得到了释放。俞丽拿的眼眶湿润了。这飞旋的音符,随她一路翩跹翔舞,见证了一幕幕动人的人生场景。 蚕蛹化蝶:小提琴汲取中国养分 1957年,俞丽拿刚从上音附中迈入大学部。小提琴专业学生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要让最普通的观众都能听懂小提琴。小组成员何占豪、丁芷诺、俞丽拿等七八人,改编出了《二泉映月》《旱天雷》《步步高》等独奏、齐奏曲。俞丽拿等来到外滩,面对熙熙攘攘的路人拉响旋律。人群马上围拢过来,不但听懂,还不停地喊:“再来一个”。 转眼到了迎接国庆10周年前夕。“上海音乐舞蹈汇演”(后来更名为“
一次,周恩来陪外国元首听完《梁祝》后,让工作人员把俞丽拿叫过来。“小俞,和你商量个事情。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去说一下,能不能改得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总理语气温和。
那晚回家,俞丽拿忐忑不安。当时《梁祝》已深入人心,俞丽拿认为它已是定了型的作品,思忖再三,觉得拉熟了的《梁祝》不能再改。她想,总理只是以个人意见和她商量,没必要大事张扬吧。回到上音,见到陈钢、何占豪,终于还是一字未吐。数月后总理又陪外宾来沪,还是那个剧场,还是俞丽拿和《梁祝》。演出结束时,他边鼓掌边看手腕上的表。宴会结束后,总理直截了当地问:“小俞,你们没改嘛,《梁祝》还是那么长。”俞丽拿有点紧张,站在那里看着总理,只是尴尬地笑。
总理沉吟了一下,笑着挥了挥手,大声说:“我不能苛求艺术家,能不能改,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看到总理的笑容,俞丽拿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此后,总理再未提起此事,以后再听俞丽拿拉《梁祝》,每次都听得很入神。
这件事,俞丽拿一直没怎么对人说。但在内心深处,她永远记得总理宽容的微笑,挥手的动作,也深切感悟到总理给她的一个启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坚持吧。
不过,周总理对《梁祝》的意见,俞丽拿其实还是考虑了。直到现在,在不同场合,她还会选择《梁祝》部分段落来演奏,这比演奏整曲短了不少,效果也很好。俞丽拿现在还会想,如果当年就能以这种方式回应总理的意见,他也是会理解的吧。
孵化蝶群:苦心培育代代新人
俞丽拿是幸运的。尽管《梁祝》后来也经受“禁拉”的劫难,但风雨40多年,她的演奏乘着“蝴蝶”的翅膀,随着200多万张《梁祝》唱片为世界所知。
俞丽拿是冷静的。一曲成名后,紧接着和上音姐妹组成演奏组,代表新中国在柏林国际舒曼弦乐四重奏比赛中破天荒地获得了第四名,她却从交流中感到了差距。
俞丽拿更是富于责任心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斯特恩、梅纽因、帕尔曼、阿卡多等大师来过上音,她贪婪地汲取经验。她说,中国小提琴家走向世界,她这一代音乐家还做不到,需要下一代、下下一代。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