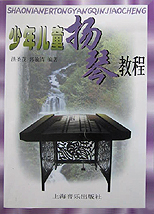海归扬琴精灵刘月宁:喜欢一件事就坚持去做
导语: 2008年8月24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中国第一场扬琴重奏音乐会为我们献上了一道音乐大餐。指导这场音乐会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授刘月宁。 30年前,刘月宁在电影《春雷》中以一曲扬琴独奏《映山红》,开始了自己的扬琴之路。30年后,她带领学生们开始走向世界。2008年6月,刘月宁在音乐圣地奥地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让我们再次对这位音乐教授刮目相看。 刘月宁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从事扬琴教育事业已有21年。人们听到“教授”这个称呼,总会有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同时会想到头发花白、特别和蔼的老人。而见到刘月宁的第一面,却感觉刘教授像一个年轻人,“颠覆”了教授的形象。 “有些人一旦喜欢上一件事后,就会坚持去做——我就是这样” 刘月宁1977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民乐演奏家。她说:“所谓的‘77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我们班当年学扬琴的不止我一个人,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从事这一行。1977年入校,1987年毕业,用了整整10年来学习扬琴。在我们这批人毕业前,民乐的教育多数都是依靠民间的传承,包括我的老师在内都是这样,而我
2008年8月24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中国第一场扬琴重奏音乐会为我们献上了一道音乐大餐。指导这场音乐会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授刘月宁。
30年前,刘月宁在电影《春雷》中以一曲扬琴独奏《映山红》,开始了自己的扬琴之路。30年后,她带领学生们开始走向世界。2008年6月,刘月宁在音乐圣地奥地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让我们再次对这位音乐教授刮目相看。
刘月宁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从事扬琴教育事业已有21年。人们听到“教授”这个称呼,总会有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同时会想到头发花白、特别和蔼的老人。而见到刘月宁的第一面,却感觉刘教授像一个年轻人,“颠覆”了教授的形象。
“有些人一旦喜欢上一件事后,就会坚持去做——我就是这样”
刘月宁1977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民乐演奏家。她说:“所谓的‘77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我们班当年学扬琴的不止我一个人,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从事这一行。1977年入校,1987年毕业,用了整整10年来学习扬琴。在我们这批人毕业前,民乐的教育多数都是依靠民间的传承,包括我的老师在内都是这样,而我们这批科班出身的音乐人是我国音乐传承的新开端。”
“有些人一旦喜欢上一件事后,就会坚持去做,我就是这样——对自己的专业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所以我一直都在坚持。”刘月宁是第一个公派到李斯特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教育的访问学者,38岁时她就已经成为正教授。在众多人都认为她会在音乐这条路上继续前进的时候,她选择了去读哲学博士。
刘月宁说:“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第二专业我选择了古琴,虽然没有这个学位,但它一直都伴随着我。这已经超过了一个民乐家、教育家本身的职业范围,但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对于人生,她也有自己的哲学思辨:“我有两个理念:第一,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永无止境。同时,人生也是一个感悟的过程。第二,因为我在匈牙利频繁地学习和交流,深受影响,我希望人们从音乐当中能够体会到对生活的感悟,这也是举办此次普及性重奏音乐会的目的之一。”
“那些与追求相悖的东西我宁愿不要”
几十年中各种国内外扬琴界的大奖几乎都被她收入囊中,而刘月宁面对获奖却十分淡然。
“其实获奖不是主要的,我不在意是否获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获奖我也做,没有奖同样也做得很快乐。”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刘月宁在中国扬琴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有关扬琴方面的各种书籍,一半都出自刘月宁之手,《东欧扬琴译文集》作为刘月宁的第一部译著即将出版。为自己的学生筹备各种各样的演奏会,也成为她近几年工作的重点。
“我一直力所能及地去做可以努力实现的事情来使我们这个学科更加丰富。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会越来越大、视野也会越来越宽。音乐会逐渐增多,影响力也会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你的学科建设就提高了。所以,我从不把音乐局限于一个空间内。”
2006年,刘月宁出版了在匈牙利举办音乐会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出版也为今天的音乐会奠定了基础。刘月宁内心对于荣誉的那种淡然、洒脱让人敬佩。她把自己和音乐完全融为一体,把荣誉形容成一朵朵鲜花:“我现在已经有很多花了,多一朵是为我增加一点闪亮,没有它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所以,那些与追求相悖的东西我宁愿不要。”
“身为中国人,学习民族乐器,目标不应该是孤芳自赏”
音乐会开始前,笔者在化妆间见到了刘月宁和她的学生,8个漂亮的女孩子,有些人跟随她已经有十几年。在学生的眼中,刘月宁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师。在2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她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我希望老师只教共性的内容,点拨学生寻找属于自己的个性。一个好的老师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越讲越复杂,那是江湖医生。尽量教给学生一些理念,让他们在其中随意发挥个性。”
在进行教学的同时,刘月宁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舞台实践。她说:“只有自己不断地进行舞台实践,才知道舞台需要什么,应该如何教育学生。”
除了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日常教学工作外,刘月宁还担任国外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每年她都会到世界各地去演出、讲课,通过这种对外交流的方式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刘月宁认真地讲:“我认为任何一种乐器都是一件表达情感的工具。身为中国人,学习民族乐器,目标不应该是孤芳自赏。应该把我们的音乐带向世界,让我们的文化通过扬琴这个载体传播出去。让音乐成为文化的载体,这是我下阶段更重要的工作。对于民族乐器,技术很重要,但文化是核心。”(吕星 文并摄)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