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徒如子的江定仙
导语:江定仙先生(资料图) 60年前,我进入位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受业于江定仙先生的门下。我学习的专业是理论作曲,当时班上有10位同学,江先生任我们的主课老师,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在他的精心教育和全面的关心下,他的众多弟子在后来新中国的音乐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也是非常显著的作用。 今年是江先生的90诞辰。在此,回忆一些往事以作纪念。 我跟江定仙先生在国立音乐院学习了5年,他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江先生30年代就学于上海音专,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作曲专业和钢琴专业。在中国音乐初创的时代,这种多专业的音乐专门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能够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得到这样高水平老师的教授和指导,可以说是当时抗战学子中的“幸远儿”。江先生的教授非常严谨也非常严格。我们学习的每一个科目。以至每一个习题的练习,都是在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合理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我们所学专业有和声、对位、曲式等科目,现在一般的教师批改学生作业,往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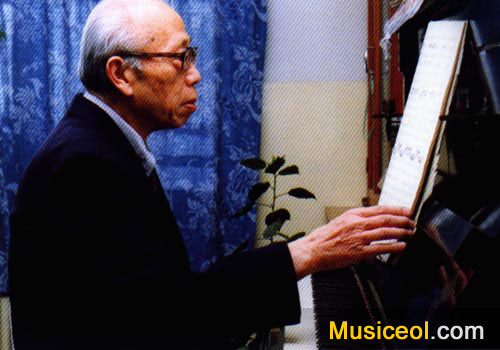
江定仙先生(资料图)
60年前,我进入位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受业于江定仙先生的门下。我学习的专业是理论作曲,当时班上有10位同学,江先生任我们的主课老师,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在他的精心教育和全面的关心下,他的众多弟子在后来新中国的音乐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也是非常显著的作用。
今年是江先生的90诞辰。在此,回忆一些往事以作纪念。
我跟江定仙先生在国立音乐院学习了5年,他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江先生30年代就学于上海音专,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作曲专业和钢琴专业。在中国音乐初创的时代,这种多专业的音乐专门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能够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得到这样高水平老师的教授和指导,可以说是当时抗战学子中的“幸远儿”。江先生的教授非常严谨也非常严格。我们学习的每一个科目。以至每一个习题的练习,都是在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合理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我们所学专业有和声、对位、曲式等科目,现在一般的教师批改学生作业,往往是老师将学生的作业拿回去,把错误标出,然后发给学生再自己看。而江先生批改作业则完全不同,除了严格给我们授课,我们的所有习题,都是由我们师生 “共同”来批改:先生亲自在钢琴上当场为我们弹奏、讲解、批改。这使我们专业的学习既扎实又灵活,非常好地训练了我们音乐专业的能力。
在当时的音乐院中,所用的和声教材,比较传统的一般都教授普劳特的《和声学》,而江先生给我们用该修斯所著的新和声教材。当时这部教材还没有翻译过来,他就对照原文当堂翻译成中文教我们学习。他还给我们留一些暑假作业,浏览该修斯的其他音乐理论著作,比如《音乐的构成》等。为了让我们接触同一学科的不同教材,还留一些原文的教材让我们在暑假里阅读,这使我们拓宽了眼界,不读死书,不因循守旧。
他在教授我们学习时,并不死板地按照“规则”行事。记得第一次交和声作业,我做的和声习题中有一个“隐伏五度”。这在和声进行中是错误的。江先生一边弹奏我的习题一边说, “这里有一个‘隐伏五度’,从规则上说是不对的,但听起来还可以”。
江先生爱徒如子。我们班上的10个学生,学习程度参差不齐,他很关心那些进度较慢的学生。因而安排进度较快的学生去辅导他们,使得同学们的关系很融洽。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先生过生日、结婚、生子的日子,江家就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师生欢聚一堂,亲如一家。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好转,学生的民主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领导这些学生运动的同学,有很多都是“江家班”的学生,他们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很有威望,江先生非常关心和支持我们这些进步学生的活动。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学生的民主运动遭到当局政府的镇压,进步学生遭受迫害。1946年学校从重庆迁到南京,学校当局借故开除了马润源、朱石林等三名进步学生,江先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学生说话,言辞激烈地与校长争吵,明确表示反对学校当局的做法。1947年爆发的“5?20”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学校当局准备执行政府的进一步行动,配合对进步学生施行“逮捕令”。在学校为此召开的校务会议上,江先生据理力争,与杨荫浏、曹安和、黄友葵、杨柏华等教授一起,合情合理地劝解校长,义正词严地向校方提出抗议,有力地阻止了他们的行动,争取了时间,使得大多数进步学生能够在国民党当局逮捕行动之前得以安全地撤离南京。
江先生还非常支持我们开展的民歌运动。1944年,以我们“江家班”学生为核心,成立了学生社团“山歌社”,探索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当时对民族民间音乐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西方音乐先进、中国音乐落后,民族音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们“山歌社”却反其道而行之,搜集我国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各地民歌,记谱整理后配上钢琴伴奏,并组织同学举办民歌演唱会,使民歌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江先生热心地支持我们的探索,对我们进行指导和辅导,还亲自为其中的歌曲配写伴奏。我们通过搜集、整理和探索,编辑了中国第一本配有钢琴伴奏的《中国民歌选》。江先生为这本歌集作序,热情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为振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所做出的点滴努力。江先生的支持使我们感到了特别的温暖。
这里,我想谈谈江先生的合唱曲。江先生写了不少的合唱作品,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我在学校时演唱过、毕业以后指挥过。其中有两首印象深刻,就是混声合唱曲《为了祖国的缘故》和《呦呦鹿鸣》。《为了祖国的缘故》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歌词的作者田间,左翼文化界的诗人,经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这首歌浸润着当时的热血青年以一片赤子之心报效祖国所特有的激愤情操和浪漫精神。这首合唱曲采用了回旋曲A-B-A-C-A的曲式结构。第一次演唱时就觉得很新鲜。当时的抗战群众歌曲,大部分结构比较简单,多是“一段曲式”,和声也比较单薄。唱这首歌时,结构曲式新颖,唱起来很有意思。A主题写抗战的激情:“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们要奋斗”,音乐铿锵有力,性格鲜明。B段的音乐描写“我们没有自由”的悲愤和悲壮,富有感染力。选择和这样的词作家来合作,创作这样的作品,表明了江先生抗战的激情和与民众同命运的世界观。江先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里的音乐家,而是心系祖国、情系民众的艺术家、教育家。
《呦呦鹿鸣》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的著名篇章。这首作品写得很有中国风味,体现了我们东方民族审美特性的典雅与和谐,旋律富有民族特色,唱起来纯朴亲切。而和声织体采用了复调的手法,使各个声部都有充分的机会担当“主角”来表现主题。大家演唱时感觉非常有兴趣。这是我国音乐前辈采用西方作曲技法表现中国民族内容的非常有益的探索。
这些生动往事使得江先生的音容时常显现在我的眼前耳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本文选自江先生纪念文集《春雨集》,2002年10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先生)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