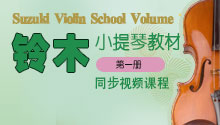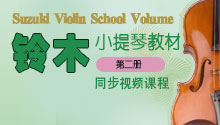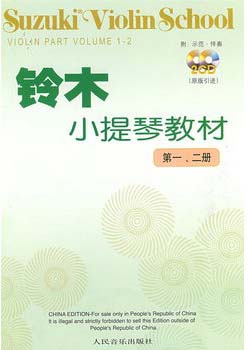郑京和星海音乐厅展大师魅力(二)
导语: 她是一位传奇的音乐家,她的出现打破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家清一色为男性的现状,成为第一位征服了西方乐坛的东方女性。她的7个兄弟姐妹中有6个人成为音乐家,其中3位享誉国际。她曾因伤隐退,63岁复出时宝刀未老,再获赞誉。同时她也是个普通人,她追星,喜欢韩国偶像男星朴有天。听到中国乐迷称她为女王,笑称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女性小提琴演奏家里年纪最大的缘故——她就是小提琴大师郑京和,10月22日她将在星海音乐厅为乐迷一展大师魅力。日前她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说给中国乐迷 叫我女王,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 广州日报:在中国,您被称为“小提琴女王”,您喜欢“女王”这个称号吗?这次到广州的演出,有人称之为“女王驾临”。 郑京和:可能是因为我是女性小提琴演奏家里年纪最大的吧,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称号,其实什么样的称号并无所谓,我很感激我的乐迷可以喜欢我。 广州日报:听说这次广州的演出,您特意为了乐迷换了曲目。这是您首次来到广州,也是十年之后再次访华,有什么期待? 郑京和:换了一首格里格的《C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只在广州和深圳两地换了这个曲目,
广州日报:您曾说在韩国受的基础教育使您建立坚定的民族情感,民族情感对您的成长、学琴有什么影响?
郑京和:民族情感除了让我在学习和练琴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动力,还让我在获得成功后有更大的自豪感。
广州日报:中国有句话叫“文如其人”,您在舞台上演奏时彪悍、外放,不过您温柔平和,与琴风反差很大。
郑京和:在我看来,在不同的状态下,就应该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要获得认可就要演出作品的精髓
广州日报:您当年替帕尔曼登台演出,广受赞誉,而后开启世界性演出生涯。演艺界似乎有很多这种替代他人演出然后一炮走红的故事。
郑京和: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机遇,但机遇并非是成功的全部。可能也是由于独奏音乐会本身是依靠一位音乐家来演奏,一旦有意外,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只能找其他音乐家代替演奏,独奏音乐会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广州日报:您与华裔小提琴家林昭亮师出同门,您认为东方音乐家的特点是什么?如今越来越多东方面孔出现在世界舞台,您认为东方音乐家获得西方认可的关键是什么?
郑京和:我认为东方音乐家获得西方认可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演绎出作品原有的精髓。越来越多的东方音乐家在世界舞台上出现,这让同为东方人的我也感觉很骄傲。而很多东方音乐家在演奏的时候,除了可以精确地捕捉到原有的精髓外,还能有独有的延展,这也是东方音乐家相比西方音乐家的特点所在。
谈音乐教育 没有母亲的栽培就不会有我们
广州日报: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家庭里能同时出现多位顶尖音乐家,而且是在与西方古典音乐渊源并不那么深厚的韩国?
郑京和: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母亲,没有她的细心栽培就不会有我们。小时候,由于刚刚经历了战争,所以家里生活相对艰苦,但是母亲仍然坚持让我们7个小孩都学习音乐,而且她的观察力很好,让我们都从钢琴开始,然后按照各自不一样的能力和兴趣来做调整,选择不同的乐器及音乐道路。虽然西方古典音乐在韩国的土壤并不深厚,但是作为亚洲人,我们其实更加善于捕捉其中的精髓。
广州日报:同为顶尖音乐家,您和弟弟郑明勋、姐姐郑明和之间会相互比较,相互提意见吗?
郑京和:我们之间常会有交流,也会一起演出或者去看对方的表演,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习惯。
广州日报:十多年前,您的母亲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她对孩子要求极为严格,现在想来,真对不起孩子。您母亲曾经是如何严厉教育您的?您如何评价母亲的教育?现在您也有两个儿子,您会像自己母亲那样教育他们吗?
郑京和:对我来说,母亲的教育其实并不严厉,只是希望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她是一个乐天派的人,善于将任何不幸的事情化为福气,小时候每次我遭遇挫折的时候,都是她给了我鼓励,让我不要有任何压力和挫败感。现在想起来,是母亲的鼓励陪伴着我一直走向成功的。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也是和我母亲一样去对待自己的孩子的。
老师葛拉米安给我的训练是完整的
广州日报:中国人很重视师承关系,您如何看待师承?
郑京和:我认为师承这一点很重要,老师几乎建构与影响了你所有的音乐历程。在机械式和功利性的音乐教育面前,我们更加急切需要的是全面性的音乐教育,好的老师能够给你系统性地建立相关的曲目,并且可以给你更为强大的音乐观点训练。
现在的学生可能为了考试或者比赛,无法练习完整的曲目,但是我当初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葛拉米安给我的训练就是完整的,一定要有完整的基础,演奏生涯才得以顺利。(广州日报/李渊航)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