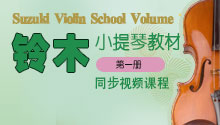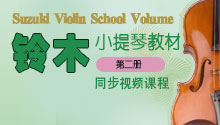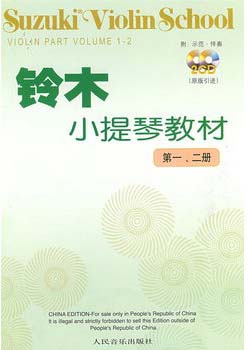朱亦兵:音乐面前 人人平等
导语:图:朱亦兵去法国二十一年后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关于大提琴家朱亦兵的故事,很多人记得的,都是十年前他拖?几百个箱子浩浩荡荡回国的场景。二○○四年,旅居欧洲二十一年的朱亦兵回到北京,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系教授。同年,组成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带领自己的十馀个学生全国各地巡演,西藏都去过了。这些演出,大多是公益性质,分文不收,却面对不少难以想像的批评和质疑。不过朱亦兵仍在坚持,因为他想改变自己,而且他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能善待自己,这个社会就也变得好了。 朱亦兵先前来港,与钢琴家郑慧合作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后,记者见到他,也听他讲了讲过去十年中某些委屈的、纠结的抑或快乐的瞬间。(以下记者简称“记”,朱亦兵简称“朱”) 当年赴法乃“命运安排” 记: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和您刚开始学琴那会儿,有什么不同? 朱:时代进步了,社会开明了很多,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在演变,虽然这种演变速度太慢。教育应该是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火车头,目前状况还不是这样。但是孩

图:朱亦兵去法国二十一年后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关于大提琴家朱亦兵的故事,很多人记得的,都是十年前他拖?几百个箱子浩浩荡荡回国的场景。二○○四年,旅居欧洲二十一年的朱亦兵回到北京,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系教授。同年,组成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带领自己的十馀个学生全国各地巡演,西藏都去过了。这些演出,大多是公益性质,分文不收,却面对不少难以想像的批评和质疑。不过朱亦兵仍在坚持,因为他想改变自己,而且他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能善待自己,这个社会就也变得好了。
朱亦兵先前来港,与钢琴家郑慧合作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后,记者见到他,也听他讲了讲过去十年中某些委屈的、纠结的抑或快乐的瞬间。(以下记者简称“记”,朱亦兵简称“朱”)
当年赴法乃“命运安排”
记: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和您刚开始学琴那会儿,有什么不同?
朱:时代进步了,社会开明了很多,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在演变,虽然这种演变速度太慢。教育应该是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火车头,目前状况还不是这样。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很好的。就像我年轻时候也很聪明,也有某种好学的慾望。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
记:您当年去法国,是因为特别喜欢巴黎音乐学院吗?
朱:根本谈不上喜欢学校,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和互联网,八十年代初从中国内地出去留学的凤毛麟角,哪谈得上了解学校,连法国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说还要讲法语。都是命运的安排,但是佛说,没有巧合,都是必然。那么,在我就是必然吧。
记:但是既然不了解,为什么要出去?
朱:说实在的,我那个年代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有一种感悟,像一种植物,觉得有些乾渴的状态,渴望新鲜的能量源泉,有这种冲动,虽然不知道大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在等待我。当时只有十七岁,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想得很远。
记:那时候出去,觉得有冲击吗?
朱: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儿晚了。这么多年过去,那些冲击都被我消化了。冲击肯定有的,特别是文化冲击,对我来讲,最大的冲击是,外面的世界是安静的。
记:中国相比而言,有一些些喧哗和浮躁。
朱:你要是觉得一些些,好吧。
记:那您当初为什么回来,既然外面的世界很安静?
朱:十年来,上百个记者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也不想编故事了,就说一句:即便在天堂里,人也有郁闷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想改变自己人生的一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些改变会带来好还是不好的结果,就是冲动,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冲动。
记:考虑了多久?
朱:一剎那。
记:回来之后发现北京变了很多?
朱:中国这个地方绝大多数的变化都是你看得见的东西。
记:所以你觉得某些东西还是在那儿停?没动?
朱:当然,根深蒂固,刻骨铭心,天长地久。就这三句话。
记:那你回来想改变什么吗?
朱:我想改变自己,不想其他。
记:但是你成立了一个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全国各地演出,听说西藏都去过了。
朱:没想改变什么,只是想维护自己的生命。当每个人都想办法爱护自己生命的时候,社会会变得很好。
记:成立乐团的初衷是什么?
朱:我们对近代音乐的理解还停留在大,大乐团大明星,这是我们音乐的现状。而室内乐组合是近代古典音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考入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后来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做首席,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交响乐团看成大室内乐。团队之间的默契,对空间的认知和感悟,这些在中国音乐教育的理念中还找不到。先进的教育不是说你浇浇水施施肥就能长出来,不是纯自然的产物,是让我们去接受去容纳我们没想到的东西。
和学生相处“没大没小”
记:你怎么和学生相处?
朱:没大没小。我和他们同台演奏,在传统教育理念中不是很合规矩的行为。我坚持认为,音乐面前人人平等。
记:但这个“音乐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实施起来会不会遇到些麻烦?
朱:会的,我们的大提琴乐团风风雨雨十年,走过了中国五、六十个城市,演了超过二百八十场音乐会。你有多大的真心你就能走多远。
记:演出都是自己安排?
朱:全是我自己。我没有助手,没有经纪人,没有宣传,更谈不上炒作。但我渴望炒作(笑),但不渴望帮忙。我从这种付出中可以得到满足,与其说我不信任别人,不如说是我自我投入的充实和满足感。我想付出,但有些时候人们觉得,想主动付出的人不正常。
记:有人这样怀疑过你吗?
朱:当然,很多年都是这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给国家领导人演出了,这种公开批评的声音才少了。很可悲。去医院,农村,孤儿院演出,有些人会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联繫学校演出,学生会说,朱老师,我们学校没有音乐厅。我说,那去课堂上演出总可以吧?几个礼拜之后,学生会的同学又回覆我,说我们学校领导说了,课堂里不能有音乐。我说,那我讲座可以吧?他们批准了。到了讲座的时候,我一边讲一边拉琴,他们也没办法。
记:很多人还是不习惯不计成本不计得失的行为。
朱:我从小有个优点和毛病,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信。有时候校方跟我说,好,朱老师,没问题,都安排好了。我就信了,就出发了,快到了联繫学校,那边说,啊,你们说真的啊,真要来啊。但我并不因为遇到忽悠的人就不相信下一个人,我一如既往地相信。
记:那您遇到的忽悠的多还是不忽悠的多?
朱:不忽悠的越来越多。
(来源:大公报)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