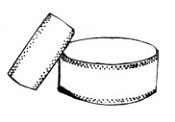张国勇:艺术家应如实反映社会,还应该不断敲打它
张国勇:艺术家应如实反映社会,还应该不断敲打它

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张国勇
采访张国勇指挥当天,碰面时间定在彩排后,大约下午三点。彩排结束,他步下指挥台,不早不迟,刚好三点整。 “我是一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
张国勇现时是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93年曾公派赴俄深造,师从指挥大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并以有史以来最高分取得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博士学位。身边接触过张国勇指挥的朋友同事,无不说他健谈,亲晤其人,方知他不止健谈,且温文谦厚,谈吐蕴藉却毫不中庸,态度分明却不露锋芒。与他交谈,有种听智者一言的亲切快意。
早前6月30日,张国勇指挥广交 2018/2019 乐季最后一场普及音乐会,台上他身着燕尾服,讲解时言辞风趣,甚至提起当年演出时的尴尬往事,当众幽自己一默;指挥时则笃定利落,有君子之风。近期张国勇为报章撰写月度专栏,论及个人经历、行业现状以及音乐教育,笔调朴实,直陈其事,展现他对文化环境的独立观察。苏格拉底曾自比牛虻,针砭麻木,呼唤良知,他说艺术家同有此责。“艺术家不应该只满足于成为社会的镜子,如实反映它;艺术家还应该是社会的锤子,不断敲打它。”
采访临近尾声时,我提出可否再问一个问题,这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却说, “可以,没问题,你问吧。”
大学毕业时第一次指挥上交的经历,你形容为 “不寒而栗” ,指挥和乐手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大团之中,是否会有一点暗自较劲的情况?
一个年轻指挥的成长过程中,与乐团的关系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乐队非常强势,年轻指挥没有实力与乐队抗衡,这个阶段其实不存在较量,因为完全不对等。为何说 “不寒而栗” ?有句话叫 “陪公子读书”,我们没有经验,你不提要求,他觉得你没有能力;你乱提要求,他觉得你根本不懂。所以第一阶段,尤其初出茅庐者,无他,就是虚心。
当你成长到壮年,迈入成熟期,和乐队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自然就出现较量。乐团成员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极具个性和思想,要说服他们与你思路一致,其实不太易。到了第三阶段,此时你已经完全成熟,阅人无数,指挥和乐队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理解、团结的关系。
(什么年纪开始意识到三个阶段的存在?)九十年代后期,我从俄罗斯留学回国后,羽翼相对丰满些,跟乐队排练难免产生理念分歧,甚至有过火药味很浓的时候。人过五十之后,我才基本明白这些道理,跟乐队之间也已形成默契,彼此了解。我懂得乐团的心理,因而鲜少再发生矛盾。好比人的成长,我们年轻时都有过愚蠢的想法和举动,这无碍我们走向成熟。一个心理健康、热爱音乐的指挥,就应该去经受挫折,从中历练胆量、意志,同时充实自我,直至有足够能量和内涵与乐队共同创造美好。
有人说, “十九世纪是作曲家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指挥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变成了乐团的世纪。” 如今乐团是否愈发成为强势的一方?
“十九世纪是作曲家的世纪” ,确实如此,几乎所有经典作品,都诞生在那个时代。当时指挥还未成体系,许多作曲家比如贝多芬、布鲁赫,创作之余也自己指挥。进入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的作品基本上已成经典,作曲家亦大多离世,此时乐界对指挥的 “二度创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还全然按照一世纪前的感觉去演奏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显然已不符合当时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
此时,世界格局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九世纪古典时期,世界没那么复杂,机器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到了二十世纪,高科技、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价值观发生剧变,越来越多流派、思想、哲学体系纷纷涌现。如此一来,若是再用单一的思维模式去解释莫扎特、贝多芬,恐怕无人买账。可见经典演绎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所以说 “二十世纪是指挥家的世纪” ,也很有道理。
独裁式的指挥在前苏联时期相对突出,指挥家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在西方,好乐团亟需像卡拉扬、富特文格勒等老指挥家的领导,以立身于世界一流。卡拉扬和乐团有过矛盾,但他对乐团的贡献无可取代。任乐团总监期间,他善用各种手腕,包括商业模式,将柏林爱乐乐团推向世界一流乐团之列。这种情况下,指挥自然权力很大,威望很高。二十一世纪,时代又变了,上一代指挥家业已作古,音乐家的维权意识今非昔比。指挥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粗暴对待音乐家,一切关于音乐的探讨都是基于尊重和平等。
然而,目前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程度与西方相比尚有一段距离,维权意识却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私以为,在一个文明程度有限的领域,有必要适当保留权威。“二十一世纪是乐团的世纪” ,我不完全认同,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是一回事,前提是乐团是否已经达到职业标准,行业整体达到标准,此话再说不迟。
举个例子,国外的职业交响乐团,排练前全体乐手提前就座,自发热身练习,待指挥到位后开始排练;大多数中国乐团都是踩着点,提前两分钟坐下来,一开始就拼命吹拼命拉,即使从运动生理学上讲,也是有害无益的。我要求自己的乐团必须提前二十分钟到位,并时常会亲临督察,《劳动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我的要求就是如此。或许他人看来这有点权威、独裁,可这对乐团走向职业化是有益的。
你觉得理想的 “乐团-指挥” 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平衡双方之间的话语权?纵观许多乐团的历史,某程度上也是一流指挥家成就了一流乐团?
对,当乐团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说实话一般指挥是很难驾驭的。因为所有作品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所有名指挥都领教过了,你无法不尊重他们。有时候你根本不必说什么他们就知道如何演奏,这时还有空间让你耍威风吗?没有了。
不过一个心理健康的乐团,亦应善于接纳新鲜事物。传统不可忽视,可我向来认为,碰到新事物时,不要急于否定,先试一试,看看是否有创意在里面。无奈天性使然,人是因循守旧的,创新要付出代价,这是惯性思维作祟。如用强硬办法威逼他人接受,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所以我每到一个乐团,发现固化的东西,首先我会尊重他们,再者我会与他们商量,看看是否有尝试的空间。例如我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时,引入交响乐思维排练,起初他们极其抵触,等他们尝到突破惯性的甜头,自然会乐意跟你一起走。
指挥与乐队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每个乐团都有自己的音响特色,每个指挥亦有其独特的诠释和概念。一个好指挥,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指挥,指挥过那么多乐团,如果真能博采众长,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指挥。很多人做不到这点,是因为不具备发现和吸收优秀事物的能力。
反过来讲,指挥塑造乐队,那是很自然的。每个乐团的演奏风格也必然会带上总监的烙印,包括音色、平衡、演奏法等等。一个优秀指挥所带领的乐团,你甚至可以凭唱片大致判断出是哪一个乐团。
另一种平衡,是指挥家自身的艺术修养,如何才能达到你所说的 “理智与激情并重” ?
箇中关系有点像恋爱。创造音乐的过程中,如果一味强调激情,自己弄得大汗淋漓,却耳不聪、目不明,相当于激情将所有东西掩盖了;反之,到了舞台上,还一板一眼全按拍子打,过分理智则会缺乏魅力,乏味无比。一个好指挥应是激情与理智的两极化,他的成熟和魅力,体现在两极之间砝码能否自如、顺畅地游走。这取决于他的工作经验及个人素养,调节失度,必然偏废。
专职指挥大约在十八世纪末开始出现,为何分工细化是发展趋势?当下作曲素养对指挥而言是否仍至关重要?
在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里,指挥系学生必须学会所有作曲课程,包括 “四大件” —— 作曲、配器、和声、复调,否则不可能深入理解作品,也无能力进行 “二度创作” 。指挥要洞察作品用意,甚至纠正错误,一些优秀作曲家会征求指挥意见,毕竟我们和乐队打交道,音响意识往往比作曲家更敏锐。
至于为何现代指挥分工更趋明确、精细?首先音乐流派越发多元,文化背景、师承、研究方向都会影响到一个指挥的风格。有人说我擅长指挥俄罗斯音乐,尤其是肖斯塔科维奇作品,因为这是我的研究方向;此外,现代作曲技法越发复杂,指挥一职已非一般作曲家能够代劳。贝多芬时代,指挥技术并不是很难,节拍四平八稳;到了斯特拉文斯基时代,一切变得复杂,配器繁复多彩、速度变化多端,你能想象贝多芬指挥斯特拉文斯基的曲子吗?
这越来越说明一个结论 —— 指挥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不仅要跟人打交道,还要对作曲技法有全面了解。
你曾数度执棒香港中乐团,并指出指挥中乐需要把握 “韵味” 与 “民族精髓”;你也素来擅长指挥俄国作品,俄国远离西欧中心,其音乐具有强烈民族特色,你如何把握这些作品的韵味?
现代民族管弦乐与西洋管弦乐存在诸多共通点,它的交响性较三十年前强化了很多。演绎这些作品时,既要运用交响乐思维,同时要把握民族乐器、配器与旋律的特性,尊重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味。一旦违背这些准则,艺术价值就会流失。
谈及俄罗斯音乐的风格,其实风格与历史渊源、民族性格有极大关系。德意志民族相对理性,盛产哲学家;俄罗斯这个地方,幅员辽阔,冬季漫长,历经战乱,这些因素造就他们刚烈、粗放的性格,自由的想象力,音乐自然有别于一般西方音乐。
他们的历史进程也迥然于西方,你想想,沙皇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到苏维埃,然后到苏联时期,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复杂。比方说沙皇时代格林卡的音乐中,你会明显感觉到皇权;苏联时期,你明显感觉到艺术家的 “欲哭还笑” ,铁幕之下,你得装呀。那个时代的音乐,情感那么丰富、深奥、纠结,与历史背景有莫大关系。
录音的产量和质量是外界评估乐团、指挥和音乐家的标准之一,但这一点似乎很难在中国实现,因为国内唱片业已经衰落了。这对国内古典乐推广是否有消极影响?
我觉得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时机,恰恰与全球唱片业的发展错开了。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交响乐进步非常快,可它已经错过唱片的繁盛时代。如今整整三十年过去,唱片业已经没戏了,取而代之是发达的网络。中国乐团并非没有能力灌唱片,指挥家余隆就率乐团录过质量可观的唱片,不过这种唱片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远大于商业价值。
多年来,唱片既推动了乐团,同时也 “害了” 一批听众。有人问我,唱片、网络这么发达,为何我们还要去音乐厅?我认为,许多发烧友并不是在欣赏音乐,而是在欣赏他们的音响。他们对音响设备津津乐道,听说一根上好的线材就要十万块钱,确实这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我个人不太主张这种所谓 “音响” 。音乐是用来打动人心的,不是纯粹感官上的舒适。
另外,你听唱片,永远是在重复 “死” 的东西。聆听交响乐,同一支乐队,交予不同指挥,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音响效果;更何况当你走进音乐厅,音乐家在台上的肢体语言、现场的艺术氛围、台上台下的情感流露,在唱片里是看不到的。
(平常会听唱片吗?)我在大学时基本上全听完了,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已经甚少听唱片。同样一首作品,我宁可把它当成一首新作,凭自己的感觉去解读。比如早前赵季平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先前已有人演过,为避免先入为主的误判,我刻意不去听唱片,结果赵季平老师非常认可我的诠释。
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古典乐界的乐评生态?
中国太需要真正的乐评,但眼下看到的更多的是报导。真正的乐评是独立、不伪言,博人眼球、哗世取宠之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乐评人。
我建议大家研究一下《纽约时报》的哈罗尔德·勋伯格(Harold C. Schonberg)。作为乐评人,他去听音乐会,向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音乐会前,当事人休想与他见面;二是从不接受赠票,都是自己买票;音乐会一结束,他就赶回报馆,45分钟完稿,发稿后,你才可以请他吃饭喝酒。这才叫真正的职业道德。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音乐家履历上的真实体现,因为他几乎是权威性、独创性的代名词,并极富个性见解。
反观中国的乐评生态,实在是不夠健康。
采访前阅读过你的一些专栏文章,其中论及个人经历、行业现状甚至音乐教育,观察和写作是你日常表达重要的途径吗?
写作是我的自觉行为。艺术家不应该只满足于成为社会的镜子,如实反映它;艺术家还应该是社会的锤子,不断敲打它。我们小时候看《牛虻》,苏联曾经把它翻拍成电影,音乐还是肖斯塔科维奇写的,里面有一句话, “上帝派我来,就要像一只牛虻一样,叮在社会这头牛身上,催牠不断前行。” 疼,牠就会走了。
艺术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我写作基本没有报酬,素日留心观察,勤于思索,既然看到,就要在不侵犯底线的情况下,说真话。为的是这份事业和不容泯灭的良心。
中音在线:在线音乐学习门户
相关内容
- 为《唐诗三百首》谱曲 刘尊让孩子有歌可唱2019-7-26
- 陈其钢、余隆:用世界音乐语言讲述中国哲学2019-7-24
- 莫华伦:“音乐没有高低之分,所有音乐都是人类的财富”2019-7-24
- 华裔指挥家黄胤灵:音乐是空气的灵魂2019-7-24
-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019年各省艺术类专业录取分数线2019-7-22
- 旅居奥地利的钢琴家张凯谈欧洲音乐艺术教育2019-7-15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