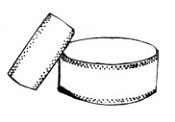指挥家卞祖善与《红色娘子军》说不完的故事
指挥家卞祖善与《红色娘子军》说不完的故事

说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著名指挥家卞祖善的名字不容遗忘。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卞祖善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在今年国家大剧院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85岁的卞祖善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再次奏响《红色娘子军》的经典乐章。除却一头青丝已变作银发,卞祖善身形清瘦,动作从容潇洒,依然是人们印象中的模样。
从流浪少年成长为新中国指挥家
1949年初,一个男孩偷偷钻过铁丝网,扒上火车。火车“隆隆”地驶出镇江,带走了金山寺、北固山,也带走了他贫苦却温暖的童年:买不起文具,父亲就带他在玻璃板上练字,写了擦,擦了写;还有至今难忘的那首《摇篮曲》,歌词里唱着“瞌睡虫来了,来了……”那一年,卞祖善13岁。父亲重病后,家境更加困顿。身无分文的他孤身一人流浪到上海,想投靠在那里谋生的哥哥。兵荒马乱的年月,哥哥也失业了。走投无路时,他被好心人送到了上海一家难童教养院,成为了唱诗班的一员。
“音乐与我本无缘,是音乐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音乐。”卞祖善的座右铭如是写。他的人生中有两次与音乐互相选择的机会,这是第一次。学唱歌的同时,唱诗班的艺术指导老师黄兰玉还教他弹钢琴。很快,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卞祖善考进陶行知先生创办、能够提供食宿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每到周末,陈贻鑫老师就会带着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坐上三轮车,去兰心大戏院旁听上海交响乐团“星期音乐会”的彩排。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那五光十色的世界,从此向卞祖善打开了大门。
1952年10月,学校合并调整,卞祖善转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少年班(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前身)。那时的卞祖善一心向着作曲努力,写过一些作品,其中,《在田野》曾由钢琴家巫漪丽录音,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成立前夕,卞祖善的耳边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学指挥吧,你看你耳朵不错,钢琴不错,音乐基础理论很好,身材也不错啊!”师长们劝道,“作曲和指挥也不矛盾,你坐在指挥台上,照样可以写曲子嘛。”
于是,音乐第二次选择了卞祖善,也成全了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乐队指挥”。“第一位”何解?原来,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成立指挥系,前者只设有合唱指挥一个专业,后者设有合唱、民乐、乐队指挥三个专业,卞祖善是乐队指挥专业一年级的“独苗”,师从杨嘉仁教授。求学的那些年里,他始终勤奋刻苦,只要有时间,就泡在唱片欣赏室里听唱片。终于有一天,管理员老杨忍不住用浓浓的山东话对他“抱怨”:“卞祖善,你还听啊,我们这儿的唱片都让你听烂啦!”
见证《红色娘子军》的幕后故事
1961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卞祖善来到北京,赴原文化部报到。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个选择:东方歌舞团、新影乐团和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我选最后一个。”卞祖善毫不犹豫,“它‘实验’,我也‘实验’。我们同步成长,蛮好的。”他和芭蕾舞还有一份不解之缘,第一次乐队实习,他指挥的就是《天鹅湖》选曲。
进团初期,卞祖善先后执棒舞剧《吉赛尔》和《泪泉》,其中,《泪泉》是新中国艺术工作者第一次独立排演外国芭蕾舞剧。工作的第三个年头,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开始了,它由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和助手李华德担任指挥。28岁的卞祖善毕竟年轻,没有参与到主创团队中,但他始终关注这部作品,排练时,他一边给前辈们添茶送水,一边观摩学习。
对卞祖善而言,《红色娘子军》是一部相当特殊的作品,到底指挥过多少次,连自己也数不清。很多人将《红色娘子军》视为他的“代表作”,以至于常有谬误产生。为此,卞祖善总是要特别澄清,1964年9月《红色娘子军》首演的指挥并不是他,而是黄飞立教授。1966年8月,卞祖善登上《红色娘子军》的指挥台,接过了原中央歌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的接力棒。话说到这里,卞祖善又要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黎国荃先生也参与了《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第三场中的“开仓分粮”、第六场中的“化悲痛为力量”的配乐就是他的手笔。黎国荃驾驭歌剧等戏剧音乐的水准,也大大提升了《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表现力。
1968年4月后,卞祖善指挥的《红色娘子军》因故中断,此后,在1970年,《红色娘子军》诞生了又一个版本。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再度复排《红色娘子军》。作曲家吴祖强兴冲冲地打来电话,希望能恢复1964年为毛主席演出的版本。这意味着要重新抄谱和排练,当时时间紧迫,未能实现,蒋祖慧导演却坚持,“第二场里,从琼花上场到结束,我都想用1964年的版本。”从此,这个兼有1970年版和1964年版的“混合版”流行至今,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仅在1993年,卞祖善就执棒53场。1994年,在《红色娘子军》问世3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35周年之际,这部作品受邀赴香港巡演,大家又兴奋又激动,事先安排的新闻发布会却突然被告知取消了。“不需要了!”对方说明,“发布会本来是为了促进票房,现在连100港币的站票都卖完了。”

耄耋之年依然奔走各地推广交响乐
谈起《红色娘子军》时,卞祖善博闻强识,儒雅却严谨,那是他对待艺术一贯的态度。早在1962年,独自执棒《泪泉》时,他就是个较真儿的年轻人。《泪泉》取材自普希金长诗《致巴赫奇萨拉依宫的喷泉》,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它讲述了崇高爱情对野蛮人的拯救;卞祖善却提出,它在歌颂女主角玛利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爱情的忠贞。
“杨嘉仁教授谆谆教导我,一个指挥家应该是当然的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半个作曲家、半个歌唱家。”恩师的教导始终在指引卞祖善。1999年底,从中央芭蕾舞团退休后,他依然奔忙,指挥演出、普及交响乐、写音乐评论文章、改编音乐作品。2010年,74岁的卞祖善乘坐航班多达83次。去年的疫情好转后,从8月开始,他带着《人类的交响乐——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讲座辗转在厦门、天津、沈阳、海口、无锡等7个城市,讲了8次。
音乐评论是卞祖善的又一方阵地,目前,他的各类文章已超过百万字,《乐海蠡测》《乐海回响》《乐海弄潮》三部文集已出版问世并将重印。卞祖善从来都是敢讲真话的人,“不一定客观和规范,但我愿意真诚地和大家交流。”2001年的那场“卞谭之争”至今被人们回味,录制电视节目时,围绕着谭盾的作品,卞祖善和谭盾展开争论,最终谭盾拂袖离去。“音乐评论不能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卞祖善的态度没有改变过,“现在的年轻人容易被西方技法束缚,缺乏自己的特点。”《黄河大合唱》《梁祝》《红色娘子军》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关键在于作曲家的创作植根于本民族的“音乐母语”。
无论普及还是乐评,都离不开知识阅历的积累。以音乐为起点,卞祖善读过很多书,德彪西《牧神的午后》可以延伸到莫奈的绘画《日出·印象》,理解李斯特《但丁交响曲》绕不开但丁的《神曲》。现在,他依然在坚持阅读。《我们同年生:大江健三郎·小泽征尔对话录》中,大江健三郎曾说,为了有智力缺陷的儿子小光,“我必须活着。”这句话让卞祖善很有感慨:“为了热爱的人和热爱的事业,我们必须好好活着,要有所作为。”今年,卞祖善已经有了更多的演出计划,10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团在扬州运河大剧院的《红色娘子军》将再次由卞祖善执棒。
85岁高龄的卞祖善,人生中有太多值得铭记的节点,可每每提及,他总能脱口而出、条分缕析。他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因为年轻人“敏感、聪慧、热情”。很多人想问,卞祖善缘何如此精神矍铄?在他看来,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言,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音乐。“是新中国让我有了学习音乐的机会。”卞祖善说,“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中音在线:在线音乐学习门户
相关内容
- 青年花腔女高音苏航受邀参加《已闻花名》专场演唱会2021-5-14
- 音乐教育家廖明飞:一个被钢琴家耽误的好导演2021-5-14
- 音乐人周传雄最新专辑上线 “流光”周传雄归来更少年2021-5-14
- 长沙市民音乐大讲堂:对话著名乐评人林声2021-5-12
- 田艺苗:音乐教育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刚需2021-5-12
- 为人民执棒!指挥家曹鹏拿起指挥棒瞬间从96变成692021-5-11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