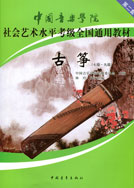“南国古筝第一人”陈安华:“弹到我不能动为止”(二)
导语: 他被称为“南国古筝第一人”,他是国家级民乐大赛唯一的广东评委,弟子遍及海内外。在古筝界有“南陈北赵”之称,而“陈”便是他,陈安华。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时而话语激烈,但稍过片刻,语气却又转到了温和。对于民乐的现状,他并不去忧心,而是“习以为常”———都抢救多少代了,最后抢救到什么了呢?他说:“这么多年过来,很多东西都看穿了。”而当记者问完最后的问题,他突然冒出了一句:“在合适的时候,我会把一些观点兜出来。” 民间的东西很厉害 记者:广东已有客家和潮州两大筝派,你为什么要重新提出岭南筝派这个概念? 陈安华:岭南的乐种有三个,广府音乐、潮州音乐和客家音乐,这三个乐种的四弦乐都是用乐谱来演奏的,古筝便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慢慢地它们都变成了古筝的专谱,古筝的曲子还是依附于潮州的弦丝乐,客家则依附于丝弦乐。 岭南有着自己的地域文化,在绘画上,我们有岭南画派,古筝其实也需要一个从地区的视域来进行归纳与整理。无论客家筝派,还是潮州筝派,都属于岭南的音乐文化,有着岭南文化的共性。当然,岭南筝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等于去
记:我们没有保护吗?
陈:从我还是孩子开始,我就不断听到“要保护,要挖掘”的呼声,但是抢救到现在,都多少代了,最后抢救到什么了呢?我们对我们的文化的重视从来是不够的,我们能否真正感受到民间音乐的魅力,生发出一种崇敬和敬畏,这个要扪心自问的。
民乐走大乐队的路子没有成功的先例
记:目前国内有不少民乐团尝试着走西方大乐队的路子,你觉得这个是民乐的方向吗?
陈: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有人这样去尝试,比如香港的中乐团。如今大陆也模仿起来,做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没有旋律感,声音强弱对比,弄在一起,不管谐和不谐和,又是强烈对比,又是高低错开,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弄什么,感觉很紧张,很怪,没有一点意境可言。
记:给人一种拼合的感觉?
陈:西洋的东西和我们中国的东西,它们的路子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以绘画作例,西洋的油画是色彩的堆积,中国则是工笔画。西方的管弦乐,就如同油画的彼此重叠,层次分明,而民乐的线条则很清楚,比如《平湖秋月》,很上口,二胡接个伴奏,现在的大乐队目前来说还没有成功的。
记:他们两者的结合,成为了一个怪物?
陈:麦当劳就是麦当劳,中国菜就是中国菜,彼此糅合可能就会是一个怪胎。这个其实就反映我们在文化心理上的自卑,西洋的好就拿来配,对不对路,好不好吃,这个必须考虑,你是在做给中国人吃,你就要看适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我们在国外受到欢迎的音乐,一定是很传统的、原汁原味的民乐,不中不西的东西,并不会太讨好听众。可能他当时会感到新奇,但是那和喜爱并不是一回事。"民族的,才是世界",这是一句实话,个性是任何一门艺术的核心之处,如果民乐在被结合、被改造后,已经不是我们当初的样子,那么民乐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
记:在民乐和外来音乐的处理上,国外是怎么做的?
陈:日本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会有两个标准,民族的东西,谁也动不得,一定要坚持最本真的东西,挖掘和继承传统的元素。而做起大乐团来,他们则是任创作者去发挥,去创造。而我们呢,传统的东西在遭到破坏,不去保存,而是去篡改,这个往往是对民乐最大的伤害。
你不懂,你发什么言
记:岭南音乐应该也是很包容的?
陈:对,岭南音乐的兼容性很厉害,外面的东西它也可以拿过来变成粤调,比如一个很哀怨的东西也可以变成街肆音乐。但是,在包容之外,对艺术最本真部分的坚持,却是少不了的。如果我们传统的东西,已经背离了音乐本身的特点,那么,所牵扯出的已经不是艺术的包容问题,而是我们对传统的一种态度。
不过说回来,艺术是讲究个性的,不过在态度上却需要包容。在有些人看来是怪物疯子,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广东民族歌舞剧团民族乐团做的《岭南变奏》,我不敢说这个是成功的路子,因为现在肯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审美观点不一样,你不可能让别人一下子去接受,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必须经过一个熟悉与理解的过程。
记: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和审美倾向吗?
陈:标准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东西。有些在当下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当它以后进入到另外一个环境,可能就成为成功的东西。
对于新的东西,我们应该支持,新的东西里面,尽管好坏杂陈,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成功的方向。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同意拿传统的东西来做实验,来改造。这仍是一个严格保护和自由创作的问题。传统的、民间的语汇,加上西洋的创作方法,把它揉成这么一个作品,就像中国菜的料子,用西洋的烹饪方法,做出来的当然就是四不像,中国人不会吃,外国人也不会吃。
不过有些东西也不能因为一次吃得不好就去否定它,新的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去慢慢接受,不能操之过急。一个作品出来,成功有几个方面,应该由历史来鉴定,所以我不敢说一定成功。比如大乐队,我们就是模仿它的,其实我们的乐器和西洋的不一样,西洋音乐每个声音都是很柔的,很沉的,尖,高,怪。如果把唢呐改得很沉,吹起来没那么尖,最后搞得很柔,没有了民乐的特点,就显得太躁了。其次,两者的音韵也不能统一,比如古筝,拉广东音乐拉惯了,西部偏低,外部偏高,这么多合在一块,又需要平均率,民间的音律虽然觉得怪,但是却是亲切的,不会给人很突兀、很奇怪的感觉。而这种音乐能不能熏陶人?可以的,但是原汁原味没有了,它变成另外一种音乐了,民间的东西很难用西洋的东西去靠拢。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乐器
古筝制作常用木材介绍
黑檀木——一般市场价6000以上 黑檀木属于高级的木材,是世界上最稀少、最名贵木种之一...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