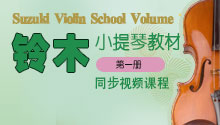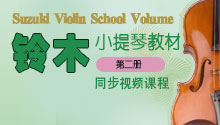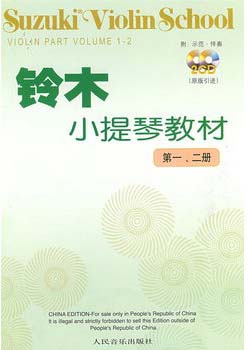纪念德国当代音乐两“H”(二)
导语: 图:哈特曼的作品曾被纳粹禁止演出 众所周知,德国音乐有三个著名的“B”─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他们共同筑起了德国古典音乐的根基。不过,有另外三位名字开头是“H”的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同样卓越─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和卡尔.阿玛丢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与三位“B”相比,这三位“H”称得上联手对德国当代音乐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詹湛 今年十二月是欣德米特和哈特曼逝世五十周年,他们两位都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辞世的。也是出于巧合,我翻出一张同时收有他们两位小提琴作品的唱片:由Supraphon出品的哈特曼《葬礼》小提琴协奏曲,以及欣德米特的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各一首。在这个晚来天欲雪的日子,将它放入唱机或许是缅怀这两位“H”的好选择。 《葬礼》小提琴协奏曲 先说说哈特曼《葬礼》小提琴协奏曲吧,它的标题“Concerto Funebre”是意大利语,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一九五九年又修订过一次,可以说是哈特曼名气最响的一部协奏曲了,而其中
至于欣德米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它的被冷落或许有点不公──当初它和萧斯塔高维契、普罗科菲耶夫和阿尔班.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一起,受到过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斯特恩等演奏家的喜爱,但是现在记得它的人似乎不多了。何故?它是传统的三乐章结构,首尾快而中间慢,开头所用调性集中于升C,结尾也是几乎与它相同的降D,可谓中规中矩。但是其风格与欣德米特的大部分严肃性极高、模仿巴赫或者布鲁克纳的作品都有所不同,作曲家用速度极快的、衔接紧密的小提琴独奏段落与生机勃勃的管乐、打击乐合奏相呼应,营造出一种戏嚯幽默的氛围。第三乐章小提琴独奏的华彩片段更是达到了情绪上的巅峰,戏剧对比程度之高甚至让人联想到了史特拉汶斯基的芭蕾舞曲,而似乎不再有传统德奥小提琴协奏曲稳扎稳打的影子了,因此可能让部分听众难以接受。然而,欣德米特在小提琴高音声部的独奏中运用的却是他最擅长的“变形”技法,也就是欣德米特《韦伯主题交响变形曲》中的那个“metamorphosis”,他也许是想借此证明,自己既然可以把巴洛克音乐信手拈来地改编为各式各样的室内乐协奏曲,又为何不能换个花样,来一次奇异、荒谬、嘲弄,又笼罩梦幻色彩的音乐版卡夫卡《变形记》(Metamorphosis)?
欣德米特同样也不为纳粹欢迎:一九三四年和一九四○年,他的音乐曾两次禁演,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是大指挥家门盖尔贝格(Willem Mengelberg)的委约之作,与哈特曼的小提琴协奏曲几乎诞生于同一年,但是它们两部作品偏偏一个真挚得悲戚戚,催人泪下,另一个却有?手舞足蹈、嬉笑怒骂的“面具效果”,同样是面对支离破碎的世界,德国作曲家们就像把策兰的黑色诗歌和尤奈斯库那部说人人希望加入变形行列的荒诞派戏剧《犀牛》摆在了一起,实在令人对德国音乐的可能性与包容性嘆服不已。
安切尔一生坎坷
最后要说一说这张唱片的演绎者:指挥家卡雷尔.安切尔(Karel Ancerl)和小提琴家安德烈.吉尔特勒(Andre Gertler)了,安切尔在捷克音乐界大名鼎鼎,大家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师承─前文提到的谢尔辛正做过他的老师,这也许是他愿意选择自己的师兄哈特曼作为唱片录製对象的原因之一。安切尔的一生坎坷多难,曾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倖存下来的人。这场唱片正录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期,安切尔被任命为捷克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从此一心扑在了指挥事业上。我们更多知晓的小提琴合作者,或许是他与约瑟夫.苏克(Josef Suk)留下的大量录音,以及与米尔斯坦留下的零星录音,但是吉尔特勒在这张唱片中的表现,完全可以和前两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媲美。吉尔特勒是匈牙利人,巴托克的朋友,同时也是纳粹的受害者。他录製过巴托克几乎全部的小提琴作品,在小提琴二重奏里也常常担任苏克的搭档。他的琴声在一方面与苏克相仿,质朴而具有穿透力,但是另一方面揉弦很克制,慢板也依旧使用小幅度、紧密的揉弦,而快板也并没有追求一味的速度,而是以颗粒清晰、节拍严谨为特色。所以吉尔特勒的质朴与安切尔棒下捷克爱乐纯美的音色汇聚到一起,颇能体现哈特曼的深邃内敛的那一面,但换到欣德米特那里,也许有些听者就觉得未尝有必要那么沉稳老成,似乎再“疯狂”一些就好了。
当然,唱片中还收有正值壮年的托特利埃献上欣德米特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确够味,比起托老与英国指挥家道恩斯(Edward Downes)一九六七年在BBC唱片录製的那张,也许是年轻十多年应该有的张扬,显出一番“诗当得意处,酒到半酣时”的醉态。Supraphon的音效生动逼真,跳弓和换弦的摩擦声丝丝入耳,更是胜过BBC一筹,不过这就是题外话了。
要是Supraphon公司把这首大协换成亨策于一九四八年创作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多好(反正按唱片时长估计,长短也差不多),因为那样一来,德国音乐的三个“H”即可在小提琴协奏曲的世界里见面切磋啦。神游云端,笑看今日世界,岂不游哉乐哉?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