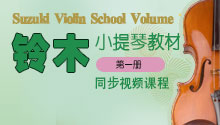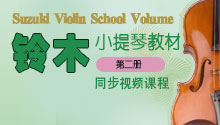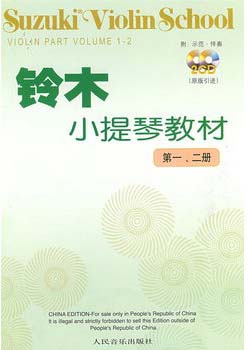陈曦:不以拉得完美为目的(二)
导语: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陈曦 陈曦是那种命中注定要拉小提琴的人。拉小提琴的父亲没有给陈曦其他后路,他刚出生被抱出产房时,父亲不是先看他的脸,而是先看他的手怎么样,一看手还不错,以后能拉小提琴。于是三岁时,陈曦就开始随父习琴。这是一条被家长规定和引领的人生之路,但幸运的是陈曦发现自己喜欢和适合。他有一份闪光的履历, 17岁时即荣获第十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银奖(金奖空缺) 。现在,他是中国唯一获得授权使用造琴大师斯特拉底瓦里在1708年制作的价值600万美元的古董名琴“红宝石”的小提琴家。在舞台之下,这个29岁的男孩,不胖也要减肥,在微博里发不同城市的天空照,感叹北京的空气质量差,调侃自己做饭不好吃。这一切,和我们身边的很多“80后” ,都没什么不同。但一谈起小提琴,他又能瞬间变为文艺男青年,分享他所理解的音乐世界。 突然发现离获奖非常近了,才紧张起来 记者:现在大家介绍你时,都不可避免会提到2002年,你参加第十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时获首奖的经历。你当时参赛时是一种
记者:后来你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陈曦:那时我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少,那是我第二次参加国际比赛,很多媒体都很关注来参赛的中国选手。我是一个人越多越兴奋的人。当时还发生一个意外,比完第一轮后,有天我去组委会参加合伴奏,那天正好是世界杯比赛,日本队对俄罗斯队,我过人行横道时,被球迷当做日本人打了。但坏事可能变好事。因为胳膊被打伤,我有将近三天没有练琴,这三天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每天都去看比赛,抱着学习的态度在现场看其他选手拉琴,在音乐的表现上自己重新拿一些主意,也是一种提高。
第二轮我去拉时,整个呼声就蛮高。进入第三轮后,我才真正紧张起来,因为突然发现离获奖非常近了,而且经过前两轮的比赛,大家比较看好我。当别人对你有期待时,就会有压力。比赛前一天,我给林老师打电话,说特别紧张,怕拉不好,他当时说了对我比赛特别有帮助的话:你就把下面的评委当成一群可爱的小魔鬼,要无视他们。这句话我非常受用。决赛时上台演奏,前几分钟还很紧张,但随后就完全没有把它当比赛,而是当成一场音乐会去拉的。
记者:比赛结束后有国外权威音乐杂志评价你:“一个拥有强烈个性、极其光彩辉煌的演奏家。 ”当时你才17岁,是如何形成自己的个性的?
陈曦:个性就是一个人对美的向往。我并不喜欢那种完全完美的,没有一点瑕疵但是没有很多个性的东西。完美是建立在一些缺陷上的,这样才能更突出它某些方面的美,如果所有的曲子都拉得像漂亮的中国福娃或年画,反而会让人觉得没有深度。我个人认为,在练琴时,在技巧上一定要以完美为准,但在演出或比赛时,我并没有以完美为目的,而是以艺术的高度为目标,要把观众领入到你的艺术世界当中,感觉到痛与快乐。
音乐没有形状,没有标准定义
记者:法国小提琴大师热拉尔·布莱听了你的演奏后说:“他用他的小提琴在向我们讲述一个故事,他很清楚音乐是什么……”能不能谈谈你怎么用小提琴给观众讲故事?
陈曦:音乐都是在表达,作曲家在写一个曲子的时候,他不是为了钱在写,没有一个作曲家是超级富有的,也没有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创作仅为好听,他们是在反映自己那个阶段的思想、心理活动。为什么贝多芬的作品经久不衰?不是因为他创作了好听的音乐,而是因为他是个情绪化的人,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能感觉到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假如我拉一个贝多芬的协奏曲,我就要知道他那段时间心情处于低谷,自杀未遂,又慢慢走向光明,而且耳朵完全坏掉了,这个时候就要把自己完全放在这个故事里。其实要站在三个高度,历史的高度、大自然的高度、作曲家的高度,去理解作品,它一定会有故事。你要设置这个故事,观众一定会跟着这个感觉往前走。
故事是有起伏的,乐句也是有起伏的,故事有时候会不明不白地结束,音乐其实也如此。比如柴可夫斯基写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表达的是他和梅克夫人之间委婉的试探。梅克夫人资助柴可夫斯基多年,两个人通了十几年的信,在信中互相爱慕,情意绵绵,但他们只在两辆擦肩而过的马车上看过对方一眼。在音乐中,能感觉到这种扑朔迷离像迷宫一样走不出去的情感,到第三乐章时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束了。幻想被打破,现实出现在面前。可以感受到,关于他们的爱情和生活,老柴自己都没有找到答案。音乐中都有故事,我们应该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二度创作。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