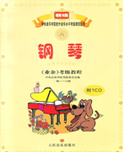钢琴演奏中影响音色表现的两大因素(二)
钢琴触键速度的快慢与基本的触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当手指弯曲得较明显时,指尖触键的过程就快、直接,离键动作迅速,弹出的声音清晰、明亮。当手指伸平时,下键动作就慢,指尖附在键盘上的倾向产生的声音就是非常连贯的音。当手指朝前伸展时触键发出的声音是歌唱的音色。但不论用哪种触键方法,都应注意手指的姿势。指尖必须要弹得透,不论音的强弱、远近、厚薄,都应让指尖落在一个点上,发出优美的音色。
用手指尖端“点”上去的音,像芭蕾舞的足尖触地,指尖与键盘基本成直角状。手指微勾的触键法,发声透明而单薄,适宜弹跳跃性强、颗粒感强的作品。而用手指面多肉指垫部位,自第二关节以下与键盘基本成锐角状的触键法,发声柔和而丰富,适宜弹奏抒情、浪漫的乐曲。抬指较高的触键法音响洪亮,较低的触键法音响或明晰或轻柔。而往往一首乐曲里要用以上多种触键法来表现乐曲的色彩,而不是孤立使用的。例如德彪西的作品《月光》,前段在和弦转换的基础上用和弦外音的方法构成旋律,并逐步扩展开来,这时手指触键低,感觉极细腻,音色要很纯净。紧接着双手和弦的这一段力度比前段稍强,双手像拍皮球似的,慢慢移动,同时手指触键高度也比前段稍高,产生的音色也就不同,表现此时的月光比开始要明朗些,中间段落速度稍快,织体变成分解和弦的流动,旋律也有较大的起伏,宁静的画面仿佛轻轻地摇曳起来,左手琶音要弹得很连贯,触键时手指力量跟着走,最后用较轻的力度,轻柔触键法再现第一段的音乐。这正如赵
晓生在“琴诀”中精辟地写道:“指触变幻,纤毫之功。疾落缓按,轻点重沉。深击浮摸,迥然不同。平指浅啜,虚声朦胧。迅发尖刺,清声玲珑。”⑺
第三节 踏板使用对音色的作用
踏板的使用是钢琴演奏中一种高难度技巧,正确巧妙运用踏板可使弹奏增加丰富的音响色彩。当延音踏板踏到底时,音色变得更加丰满,产生连贯的、浓厚的、洪亮的声音;三角钢琴的弱音踏板使用时琴槌的击弦比通常情况减少一根,从而使得音量减弱。不过与此同时音色也在起变化,踩了弱音踏板后,槌排移动了,触弦的是槌的柔软处,结果会产生朦胧的、暗淡的、轻柔的色音。踏板踩下的深浅对音色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乐曲对音色、力度的具体要求,可采用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全踏板及抖动踏板。比如将延音踏板踩下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深度,制音器与琴弦便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使音色处于半丰满状态。在实际演奏中可用于快速跑动音符的非连奏。
在不同作品中我们要结合具体作品的特点通过踏板的运用来追求音色的变化。德彪西的《月光》自始至终结合使用弱音踏板与延音踏板,维妙维肖地描画出月光笼罩的幽静朦胧的自然景色。李斯特的《狂想曲》大量使用延音踏板,浓墨重彩地渲染出管弦交响的壮阔声势。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第三乐章恰当地使用抖动踏板,较好地解决了一方面必须大量使用延音踏板以求获得一定的音响洪亮度,另一方面又须避免浑浊以求获得音响清晰度的难题。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踏板的使用一定要合理慎重,不可滥用,用得合理时会使乐曲增辉添彩,用得不好时会弄巧成拙,造成音色浑浊、脏乱。在弹奏时要根据乐曲的需要,正确巧妙地使用。
第二章 演奏者心灵因素对音色的作用
音乐之所以呈现无限的丰富多样性,其根本原因是音乐的表现力是具象性和抽象性的统一体。音乐的具象性使我们拥有一个表现和欣赏的基础,而抽象所导致的模糊则带给我们极大的自由。也许正是后一点,才使得音乐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演奏家可以对同一作品做不同的演绎和把握。您一定听过格伦·古尔德弹奏的巴赫,您也一定听过罗萨琳·图雷克演奏的巴赫,虽同是演奏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演奏风格和声音却大相径庭。正如赵晓生先生所说:“琴者一器,声色无穷。”⑻这一切,实质上是演奏家运用心灵对音色炉火纯青地控制的结果。所以说,除却技巧方面对钢琴音色的影响,艺术家的艺术心灵也是至为关键的。因为说到底,钢琴不是自鸣钟,它的发声是必须依赖演奏者的存在;而钢琴演奏者也不应该是流水线上的“纺织工人”,重复完全程式化的动作。钢琴的音色表现,在技巧方面要受弹奏力度、触键方式、踏板使用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最终实践主体还必须是人,是演奏者,是演奏者的艺术心灵,他的想象力、内心听觉和音乐素养。
相关内容
- 如何避免练习钢琴时的不良习惯 2014-11-24
- 如何防止过度练习产生的伤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对摄像机你该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演奏文凭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9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8级教材目录2014-11-17
热点文章
乐器
钢琴的发展史
钢琴(piano forte或forte piano),简称piano,是一种键盘乐器,用键拉...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