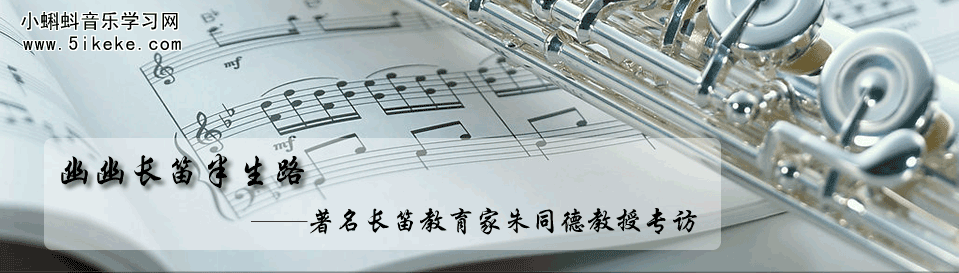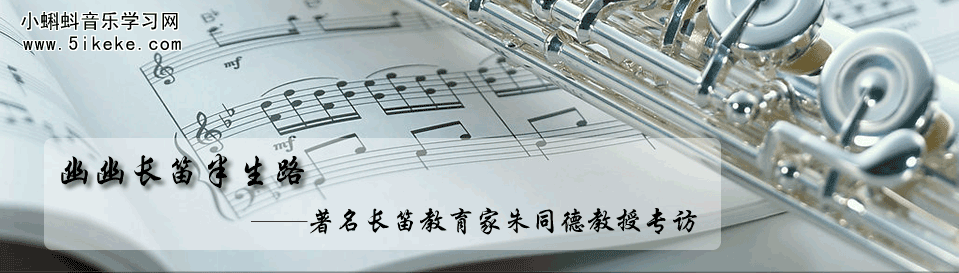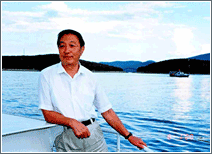1959年,身为大三学生的朱同德又遇到了一个机遇——考出国。在那个年代,出国对于一名普通大学生来说是不敢想的奢望。当时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参加出国考试的资格,都是由学校指派。学校不仅要考虑能力,而且还包括家庭成分等各方面都要考虑。朱同德很幸运地被选中了,因为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出身非常好,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朱同德清楚地记得,那次考试非常严格,全国最高的音乐家担任评委,包括李德伦教授、吴祖强教授、上海的贺绿汀老师等。这些国内所有的大音乐家担任着考试的评委足矣看吹那次考试的严格程度,不仅是学校,包括国家都非常重视这次选拔。但是严格的考试并不影响朱同德的发挥,朱同德很顺利地考上了。相比于朱同德当年考大学时的往事,这次出国就显得非常轻松。学校当时非常配合,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学校还专门派了一名俄语老师每天教考上的学生俄语,当时就连《俄华大辞典》都是学校给买的。后来学校感觉学生们的俄语还是提升不够,就专门将朱同德和同学们送进了北京外语学院进行专门的俄语学习。朱同德说:“当时在魏公村的外语学院整个强化训练了一年,这才感觉到像是真正开始上学,在上大学。每天起床做早操、背单词、吃饭,白天上课,晚上复习,每三个人一个辅导老师,每个礼拜都这样,礼拜天就上颐和园去背单词。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每个人都因吃不饱而浮肿,但是对我们学音乐的学生却是非常照顾,尤其是学管乐的,每天两个鸡蛋,还有牛奶。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没有国家的支持与培养,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在旧社会,我只是一个苦哈哈的农民子弟,哪能受到这样的待遇?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是去出国读书了。”
朱同德因为参军,高中的课程并没有学习,所以大学一连上了八年,其中包括在苏联的四年。
到苏联后,朱同德心怀着对祖国的深切感激,便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中,希望回国后能为中国的音乐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解放之初,中国的音乐教育存在两个系统:一个东欧一个苏联,当时中国的教学模式大多还是按照苏联的教学模式。所以,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音乐水品相对来说还算不错,但是在软件硬件的差别还是比较大。朱同德到了苏联后,在专业上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而且苏联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几乎没有任何干扰,只是单纯的上课与学习,尤其是寒假暑假都很长,大概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朱同德完全用来学习。朱同德回忆道:“在苏联时,学习时间的很多,只要你有时间,你想练习多长时间都可以。虽然国家之间开始紧张和敏感起来,但是同学和老师对他们还是非常友好。每个月可以在学校领到50卢布的生活费,节省一些一切花销就都够了,虽然生活不算富裕,每天吃最便宜的饭,或者买点面包抹点黄油,也能吃饱,还是要比国内的生活好一些。期间我曾回国2次,一切费用都是国家承担。中国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这在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那可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连领导人都吃不饱饭,我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能不感动吗?要不我一直在说,没有国家的培养根本不可能会有我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