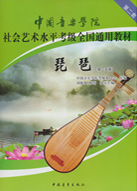演奏家张强畅谈琵琶演奏艺术(二)
导语: 相关链接:中国音乐学院琵琶考级视频课程 《 少年儿童琵琶教程》视频课程 琵琶演奏家张强 6岁开始学习钢琴,9岁随父张棣华学习琵琶。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先后师从吴俊生、邝宇忠、李光华、陈泽民等先生……作为当代著名的琵琶演奏家,现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的张强,以其精湛的琵琶演奏技艺活跃于海内外的音乐舞台。 在乐迷眼中,张强是实力超强却毫不张扬的琵琶天王;在同行看来,张强是低调内
准 技术精准度为音色加分
广州日报:有网友推荐对着镜子练习,自我纠错,这是否有效?
张强:有一定矫正作用,但我不提倡一直那样,就像我让学生不能一直用节拍器一样。那些始终只是辅助手段,演奏者最终都必须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因此心里必须有一个声音。同时,不能只重动作,而忽略了耳朵,必须提高耳朵对声音的分辨能力。
广州日报:琵琶分文曲、武曲、文武曲,这是不是它与其他民族乐器特别不同的地方?
张强:是琵琶特有的,但也特指传统乐曲。传统乐曲中,文曲重于刻画人的内心活动,单音比较多,注重左手的技巧使用;武曲重于表现事件、场面,如《十面埋伏》,音响效果宏大,注重右手技巧的发挥,如扫、拂等。
广州日报:古诗对琵琶曾有“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描述,这是怎样做到的?
张强:例如《十面埋伏》的第一声,在快速地扫弦,制造出令人震撼的声响之后,手部动作止住,但乐器却没有,余音会空中振荡。这种效果其实现代技法更可以表现。
广州日报:您很注重民族音乐的创新与西方音乐的融合,能举例具体谈谈吗?
张强:整体来说,现在民乐创作并不太多,但还是经常会有好作品。只是很多作曲家并不是十分了解民乐的具体技法,所以,演奏者就必须对作品二度创作,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为之添加合适的传统韵味。民乐的最大魅力就在于韵味,技术只要肯练都可以掌握,最难还是在于如何运用技术来表现音乐,打动、感染欣赏者。
广州日报:能跟读者分享一下您的“杀手锏”吗?
张强:完美的音色——纯净的声音、弹性的颗粒感同时又有流畅感,是我始终追求的,这与右手击弦速度、角度和松紧度都有直接关系,弹不好就会显得嘈杂。要出好音色,必须增加技术的精准度,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点上,用合适的力把弦击响。我的经验是“三多”——多听、多实践、多选择。我听的音乐很杂,古典、现代,不仅器乐,也包括歌剧、流行、爵士等等。
韵 注重余韵留白而不苍白
广州日报:您曾成功诠释过盛宗亮的《南京!南京!》、谭盾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演奏这些现代作品和古典名曲有什么不同,是否需要加入一些现代情怀、现代技法?
张强:民乐讲究韵,把技巧融入音乐是很难的,主要靠经验。我会经常听些老唱片,一些琵琶老先生留下的音响资料,例如阿炳的。虽然几十年前的民乐技术远不如今天,但他们演绎的那种味道,是现代演奏者很难做到的。
传统琵琶在左手行韵中产生美感,而现在右手的技巧千变万化,讲求速度、利落,新技术的开放、丰富,可以说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例如刘德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明的“反弹”技法,即像吉他一样往里弹,从训练角度讲并不难,但延伸出多种指法、组合,创造了传统正弹所无法完成的声响效果。
广州日报:对《霸王卸甲》、《十面埋伏》等琵琶名曲的演绎,您有什么独特的心得吗?
张强:例如《十面埋伏》,它的可变性很大,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版本,甚至同一个人的每一次演奏都不一样。有人突出场面,有人强调技术;不同性别的演奏家往往也不同,男性会更刚强。而我的版本是在“汪派”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删改,注重结构感,音乐层次清晰。又如《霸王卸甲》,我同样延续了“汪派”的质朴,不寻求大起大落,在平铺直叙中给人以规整感。
广州日报:这么多年,有没有曾让您觉得难的作品?
张强:正如拉《流浪者》容易拉《二泉映月》不容易;肖邦、李斯特好弹,莫扎特、巴赫不复杂却很难弹一样,琵琶的现代作品往往难在一种技术,练好了就能攻克。相对而言,我觉得传统乐曲更难。例如《海青拿天鹅》,音乐篇幅长、段落多、技术复杂;又如《月儿高》、《平沙落雁》,结构很多起承转合,气息、段落、指法的使用、速度的变化都很讲究,尤其是单音余韵,留白而不能苍白,让人往往难以上手,如果是一串音,反而好弹了。
广州日报:您曾参与录制了《风月》、《大宅门》等许多电影、电视剧的音乐,用美妙的乐音为这些作品烘托出气氛,录制这些音乐和平时做音乐会的演出有什么不同的讲究?
张强:环境和背景不一样,作曲家提供的往往是速度和旋律线条,要把符合乐曲线条的技术编进去,就像给有底的画上色。此外,麦克风是一个放大镜,它会把演奏者的优缺点都突显出来,而舞台往往不行。我很喜欢将录音棚当作自己的镜子,技术运用是否合适、合理都可以到那里去验证。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