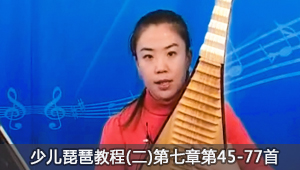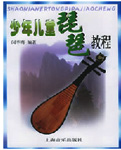琵琶演奏家教育家、汪派传人郝贻凡(二)
导语: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内蒙广播文工团要筹建一支交响小乐队,打算在包头市招收学员。在内蒙古包头市各个中学的数万名学生当中,他们选中了一个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眼睛少女,她就是就读于包头市二中的郝贻凡。 “那年我15岁,当时我刚与包头市歌舞团的李凤桐老师学了半年琵琶,只会弹一首《解放军进行曲》,”郝贻凡笑着回忆着。就凭着这样一首曲子,郝贻凡幸运地走进了专业艺术团体。文工团团长看郝贻凡手的条件不错,本打算让她去学小提琴,后来又说,“既然招你来学习琵琶,你就先去北京拜师学艺吧。”于是家里人开始四处为郝贻凡联系琵琶老师,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哥哥的一个好朋友认识北京某乐团弹琵琶的老师。于是郝贻凡兴冲冲地打点行装来到北京,见到了这位琵琶老师,他就是著名琵琶演奏家李光祖先生。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在李老师的指导下,郝贻凡的艺术才华和音乐悟性被充分调动和挖掘出来。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她的琵琶弹奏技艺有了很大的长进。当她返回内蒙广播文工团的时候,人们对她的琵琶弹奏已经刮目相看了。团长没有再提让郝贻凡学习小提琴的事情,而是对她说,你就搞琵琶独奏吧。从此,郝贻凡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期间,她师从李光祖、王范地、林石城等教授,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在大师们的影响下空前提高。但她也坦率地承认:“因为上小学和中学正值‘十年动乱’,文化衔接没接好,因此上大学感觉很吃力;再加上国家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大学教育刚刚恢复,老师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好在郝贻凡的那一届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拼搏。
大学四年虽然艰难,但郝贻凡咬着牙挺过来了,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郝贻凡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阶段该干什么就要干什么,她时常告戒女儿:该学习的时候你没学习,失去的机会你一辈子也补不上;即使你以后再学,也不如当初学起来有效果。
承受压力不辱使命
早在1987年,郝贻凡就在广州白天鹅录制了全国乐器界青年演奏者中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在全国反响很大,因此许多港台学生慕名向郝贻凡学习琵琶。郝贻凡还是大陆自文革之后第一位受台湾之邀、文化部派出的第一位青年琵琶演奏家,那是1992年,她分别在台北和高雄举办了琵琶独奏音乐会。说起十年前那次赴台演出的经历,郝贻凡记忆犹新。去文化部、外交部、从办签证、赴台手续等一系列证明前后都是一个人跑。等一切手续都办下来时,离演出的日期十分近了。压力之下,方显出一个人的实力,也考验着人毅力和承受能力。郝贻凡说,到了台湾她一下飞机就奔音乐厅,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就抱着琵琶上台了,时间紧张得简直令她连滚带爬,但那是“第一次,咬着牙也要上,因为没有退路”。带着文化部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使命,郝贻凡的赴台演出反响极好,台湾各大媒体为此做了大量图文报道。鉴于郝贻凡的出色表现,她因此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1993年度“沈心工”优秀青年教师奖。
郝贻凡先后在国内和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访问演出,拥有大量在国内外演出的舞台实践经验;而这些舞台经验又为其在教学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当她把这些舞台经验再运用到教学中之后,对学生来说就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学习效果。她说,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教学生,学生学到的东西比较扎实。郝贻凡在音乐学院接手的第一个学生樊薇2002年参加文化部首届青少年乐器独奏比赛获专业组金奖。提起恩师,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说,郝老师教学上最用心,讲课细致;平易近人,很有人情味。她不限制学生学习其它派别的东西,而是希望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各种门派的知识。她说,老师把舞台的经验应用到教学中非常好,舞台的状态感对学生很重要。樊薇能够在全国大赛上获奖,不知是否也得益于郝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传递给她的舞台状态感呢?
钻研教学寻找突破
郝贻凡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分别和浦东派代表人物林石城先生、平湖派的匡宇忠先生及汪派李光祖先生学习琵琶。她说,平湖派是白描式的,文曲、武曲都很清淡,文人气息很浓;汪派比较大众化,易于被人接受;浦东派和汪派区别稍大,花俏一些,受江南丝竹影响最多。郝贻凡说,她自己的性格跟汪派较为接近。她把汪派和浦东派的特点融在自己的演奏和教学当中,正如浦东派大师林石城先生对郝贻凡说的:你学东西是两方面的(汪派、浦东派),互相渗透。郝贻凡说,如果纯是浦东派,大家听起来就会感觉太单一了;如果一味弹汪派,又缺少江南丝竹的那种韵味。郝贻凡演奏功力深厚,与她的人一样,在演奏风格上也同样追求淳朴自然,用心诠释着传统音乐的内涵,赋予琵琶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她继承流派但不拘泥于流派。她说:“我教学最大的优势是能从汪派的演奏功底入手,也把很多西洋的技术融到我的教学中。”她接着说,过去人们说,“非从古谱入手不为工”。古谱这种工夫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但要想人人都有所突破,必须在专业训练上寻找到突破点。在这方面,郝贻凡积累了不少经验,她以及她的学生对音乐的处理上的感觉比别人舒服,因此她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学生在技术上没有障碍,学生在艺术上的训练和传统功底上的训练两者结合得比较好。”郝贻凡不排斥传统的,同时也能把新的东西融入到教学中。许多老师对郝贻凡的学生评价道:心理比较健康,技术比较健康。这是对郝贻凡教学成绩的最大褒奖。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