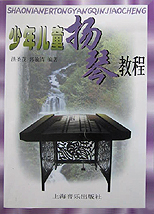刘月宁:琴曲悠扬传播中国文化(二)
导语: “我认为任何一种乐器都是一件表达情感的工具。身为中国人,学习民族乐器,目标不应该是孤芳自赏。应该将中华民族的音乐带向世界,让我们的文化通过扬琴这个载体传播出去。” 2008年8月24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中国第一场扬琴重奏音乐会为我们献上了一道音乐大餐。指导这场音乐会的正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著名扬琴演奏家刘月宁。音乐厅内观众座无虚席,翘首凝神。 听,耳边是什么在流淌?那抑或是婉约缠绵,抑或是悠扬恢弘的优美旋律,恰似春水奔腾不息……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深深感染了在场的中外观众。 30多年前,刘月宁在电影《春雷》中以一曲扬琴独奏《映山红》,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30多年后,她带领她的学生们开始走向世界。 享誉音乐界的“扬琴精灵” 还记得1977年,那个怀抱着美丽扬琴梦想的小女孩独自一人来北京参加考试,一曲《映山红》倾倒了在场所有的考官,刘月宁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参加了当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春音乐晚会,后来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在国内外民族器乐大赛中多次获奖,享誉海内外,被音
刘月宁是中国第一个公派到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教育的访问学者,38岁她已经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在众多人都认为她会在音乐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的时候,她又选择了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刘月宁说:“因为对中国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情有独钟,第二专业我选择了古琴,虽然国内还没有这个专业的学位,但它一直都在伴随着我,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多年来,国内外扬琴界的各种大奖几乎都被她收入囊中,而刘月宁面对荣誉却十分淡然。“其实获奖不是主要的,我不在意是否获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获奖我也做,没有奖同样也做得很快乐。”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刘月宁内心对于荣誉的那种淡然、洒脱让人敬佩。她把自己和音乐完全融为一体,她把荣誉形容成一朵朵鲜花:“我现在已经有很多花了,多一朵是为我增加一点闪亮,没有它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所以,那些与追求相悖的东西我宁愿不要。”
刘月宁在中国扬琴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在音乐教育方面有关扬琴的各种专业书籍,许多部都是刘月宁编著完成的。教学之余,为自己的学生筹备各种音乐演奏会,努力传播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成为她近几年工作的重点。
她告诉记者:“我一直力所能及地去做可以努力实现的事情,来使我们这个学科更加丰富。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交流的平台会越来越大、视野也会越来越宽阔。随着音乐实践逐渐增多,中国民乐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中国民乐学科建设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所以,我从不把音乐局限于一个空间内。”
音乐是人类情感的共鸣
“扬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世界扬琴分为三大体系,欧洲扬琴体系、西亚南亚扬琴体系以及中国扬琴体系。扬琴本身是一件世界性的民族乐器,而中国扬琴无论在演奏方法、音乐风格、流派技法和乐器型制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音乐语言。因此,扬琴的‘走出去’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刘月宁说。
“音乐能够最有力地唤起人类共同的智慧。”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院长鲍道•安德拉什博士在给刘月宁专场音乐会的题词中这样写道。
“民族音乐‘走出去’,真正被国外观众接受和喜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月宁的眼里闪烁着自信和大气的光芒。这一刻,你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水样柔弱的女子。
曾有一位匈牙利青年找到了刘月宁。他酷爱中国音乐,还特意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晓峰。他甚至组织了一个中国民族室内乐队。刘月宁被感动了。从扬琴到古琴,从笛子到二胡……她开始从最基本的调弦教起,有时甚至是边学边教。“在国内,我去教这些乐器大概是误人子弟,”她笑了,“在当时,看到这些迷恋中国音乐的外国朋友,只想把自己会的都传授给他们。我觉得我不再只是一名音乐老师,而是一位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者。”
现在,这个远在匈牙利的中国民族室内乐队已初具雏形。
在瑞士的扬琴制作场,在乌克兰的偏远小城镇,在捷克、斯洛伐克美丽而古老的音乐圣地……刘月宁让中国的扬琴曲声飞扬。二重奏《狐舞》、巴托克的《罗马尼亚舞曲》、匈牙利民间音乐和中国名歌《乌苏里船歌》……这些乐曲首次用中西两种同宗乐器同台合奏。欧洲扬琴——钦巴龙与中国扬琴艺术相映成辉,浑然天成,中西音乐各自鲜明的民族风格令各国观众印象深刻,叹为观止。
刘月宁与国际同行之间的技艺切磋,与异国民众之间的真诚交流,让人们不仅认识而且加深理解了中国音乐,同时也加深理解了中国文化。
在乌克兰一个深山小镇,一位中年妇女在音乐会后走上台来,流着热泪紧握刘月宁的手,久久不肯松开。“音乐没有国界”,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朱祖寿说。
“是的,在一些地方,语言不通,音乐就是桥梁。”刘月宁说,“这是人类情感的共鸣。你不能不感动。”琴声拉近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心理距离。
让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
刘月宁和她的扬琴梦想已迈出了重要一步。如今,在她走过的亚、美、欧20多个国家中,大众对中国扬琴已不再陌生。而在中央音乐学院,扬琴专业的学生也开始在她的指导下学习演奏欧洲扬琴钦巴龙。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