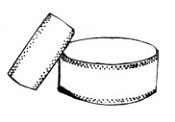普罗柯菲耶夫《第七交响曲》(二)
导语: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SergeSergeyeviChProkofiev,1891—1953)是20世纪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与指挥家,1947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艺术家”称号。1891年4月23日生于俄国乌克兰山区的伊卡特利诺斯拉夫省松佐夫卡村,1953年3月5日卒于莫斯科。他一生共创作了七部交响曲,《第七交响曲》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作品之~,同时也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该作品创作于1951年底,是普罗科菲耶夫(以下简称普氏)打算为儿童广播电台写的一部交响乐,作品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和活力,是一部非常诚挚抒情的交响乐,因而也被称之为“青年”交响曲。1952年10月11日,由全苏广播乐团演奏,萨莫苏德指挥在柯隆音乐厅首演。1957年4月,当列宁奖首次涉及到文艺领域时,《第七交响曲》首次荣获这一苏联文艺的最高奖赏——列宁奖金。 对第七交响曲》在历史上始终伴随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它过于简单,甚至说它是“非交响乐”的范例,如对普氏的天才衷心赞佩的奥林·唐斯就称“《第七交响曲》是一种后退而不是一种进步”。而苏联评论家则认为它是一部炉火纯青的杰作,如肖斯塔科维奇在1952年11月12日的《苏联艺术))上写道:“《第
从整体上来看,《第七交响曲》在和声上显得单纯而明朗,织体上显得简洁而清晰,管弦乐配器则更是音色绚丽、奇彩万千。然而决定交响曲抒情性的关键因素则是他那秀丽清澈、动人心弦的旋律。旋律是作曲家创作的心声,是他音乐抒情性的灵魂。它们从容流露,正像普氏其他晚期作品一样,旋律幻想的无穷无尽实在惊人。比如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特别是再现部的副部主题)具有宽广的音域,音区落差可达两个八度以上,这就使得他的音乐具有气息宽广、开阔的特点。但是这里丝毫没有人为的自我陶醉和情感沉沦的过度的浪漫主义特征,而是采取了适度的、理智的和普遍的感情。正所谓“本色中见奇丽、质朴里显激情”,这种客观的抒情性正是《第七交响曲》感人的艺术魅力所在,它讴歌着对青春的愉悦之情。普氏是一位抒情大师,“抒情走向是他作为20世纪作曲家最独树一帜的傲人之处。”
二、《第七交响曲》的灵魂——民族性
对于普氏的艺术观来说,他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与由此产生的在音乐中对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强烈追求。他永远以自己从属于俄罗斯文化而感到骄傲,捍卫着俄罗斯在现代音乐中的主导作用。在侨居国外的漫长岁月中,也并没有动摇普氏对俄罗斯的爱。他从国外寄回来的信中写道,“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把我引向俄罗斯。”在《第七交响曲》中也浸透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因素,这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也是最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正因如此,所以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这种创作中的俄罗斯民族风格,既表现在他的旋律与和声的特征方面与民间的和古典的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表现在他的音乐形象的个性方面,时而是壮士般的雄伟,时而是矜持的抒情,时而是尖刻的嘲笑与挖苦。俄罗斯民族特征还明显的流露在采用民间悠长歌曲特有的旋律发展的歌腔变奏手法上:也流露在多方面接近俄罗斯“交替调式”的透明的自然音体系上:还流露在倾向于有时接近民间支声性的自由复调上。这种民族性还表现在他面向俄罗斯童话故事,面向俄罗斯民歌,面向俄罗斯生活,将俄罗斯民族本质的英雄主义得以史诗性的表现。
当然,普氏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同时并没有主张民族关门主义,他对于其他民族艺术产生的主题、题材、音乐形象与俄罗斯的主题同样感兴趣,甚至在体现非俄罗斯的生活场景时,仍然保持自己创作的独特的民族素质。《第七交响曲》中的民族色彩,不仅具有民族思维的特性,也还突出自己的创作臆想的个性。作曲家通过民族风格走向现实主义、走向表现更大的真实。肖斯塔科维奇曾说:“普罗科菲耶夫为俄罗斯音乐文化做出了重大无比的贡献。他作为一位天才作曲家,发展了俄罗斯古典音乐大师格林卡、穆苏尔斯基、柴科夫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和拉赫马尼诺夫留给我们的创作遗产。”
相关内容
- 如何避免练习钢琴时的不良习惯 2014-11-24
- 如何防止过度练习产生的伤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对摄像机你该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演奏文凭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9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8级教材目录2014-11-17
热点文章
热门标签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