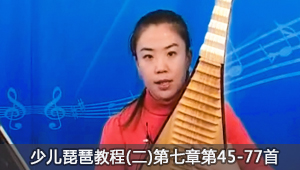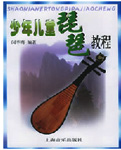浅析“琵琶”于《琵琶行》戏曲改编作品中作用的变化(二)
导语: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向来被誉为唐诗之翘楚,世代传诵不绝,元明清时期,更被作为戏曲题材加以改编,并搬上舞台。而“琵琶”这一中心道具在《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剧作的故事模式,主题中心的不同,又使得这中心道具的功效,包含的意蕴,表达的情绪,情感的张力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就作品的故事模式来看,马致远的《青衫泪》和顾大典的《青衫记》是属于同一体系的,讲述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交往,而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裴兴奴被茶商骗婚,也带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闻兴奴琵琶声,二人重逢。最后白居易复官,与裴兴奴奉旨成婚。而《青衫记》除却描写白裴的爱情,又增加了白妾樊素、小蛮与裴兴奴之间的纠葛,情节趋于复杂;同时更以一件青衫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借此大做文章。 而蒋士铨的《四弦秋》则完全摒弃了《青衫泪》和《青衫记》的爱情故事模式,严格的按《琵琶行》诗作原意,参照了《新唐书》元和九年、十年史实及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所提供的材料,淡化了男女之情,以琵琶女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通过对琵琶女的悲凉身世的感叹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众多胸怀不凡
在《青衫泪》与《青衫记》中,琵琶的抒怀作用,主要集中于表达裴兴奴对白居易浓烈的思恋之情和迫嫁茶商的愤恨之情。裴兴奴情定白居易后,便心心念念嫁其为妻,不料,婚事未成,白居易却被贬为江州司马,从此二人两地相隔,兴奴自然情难释怀。而后,更因鸨母贪利,迫其嫁与茶商,兴奴更是悲愤不已。在船行至江州时,兴奴触景伤情,睹物思人,方借琵琶抒己思恋愤懑之情。于是,便有了如下桥段:“(旦抱琵琶上)影似白团扇,调谐朱弦琴。一毫不平意,幽怨古犹今。奴家方才闭上舱门,拒绝那厮,且喜他使性,上崖去了。如今再上船头消遣一回。你看江深夜静,月冷风清,好凄惨人也。前日闻得白相公谪宦江州,此间正是江州地方。咳,只在一处,不能勾厮见,好苦呵!稍水那里?(丑扮船家上)随风倒舵,顺水推船。裴娘有何吩咐?(旦)稍水,你把这船头对着月色,就泊在这芦花岸边,待我把琵琶自弹一曲。(丑诨下。旦)碧海青天无限恨,等闲拭泪付琵琶。”
在《四弦秋》中,琵琶抒怀的内容,完全不同于《青衫泪》、《青衫记》的相思之情,主要表达的是琵琶女花退红对易逝韶华的感叹,独守空闺的悲凉,和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壮志难酬的苦闷。花退红本为京城名妓,年老色衰后,嫁与浔阳茶商,商人重利轻别离,常外出贩茶,独留退红独守空闺,只得于百无聊赖之际,忆少年情事,感芳华易逝,伤孤独难眠,不禁叹道:“咳!天长岸阔,草长莺啼,只好守着琵琶过活也呵。则这答江水九条斜,准备着泪珠儿一样泻。”而后,花退红月夜弹琵琶,琵琶声引白居易,二人相识,引为知音,退红便借琵琶向众人叙己年华不再之悲,独守空房之凄,而白居易更由这凄怆之音,联想自己怀才不遇,甚是悲愤,不觉泪下沾青衫:“盛衰之感,煞是伤心也。”而这也恰好道出了《琵琶行》的原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三、重逢
“琵琶”在《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品中,除却上述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白裴二人重逢团圆的重要工具。这一作用仅在《青衫泪》和《青衫记》中有所体现,《四弦秋》中全不涉及,这主要与两者的故事模式不同密切相关。前者是士子、妓女相恋的爱情故事,白裴二人因琵琶相识相恋,分离后又因琵琶重逢而终成眷属,以琵琶为重要道具,贯穿全剧首尾,形成一个“相识—离别—重逢”的戏剧框架;同时,也符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于大团圆结局的期盼心理。而《四弦秋》并不是爱情题材,白居易和琵琶女之间并无男女之情,也无离别之恨,二人只有“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之悲,和沦落风尘、壮志难酬的沦落之恨。因而,不论从故事情节,还是情感需求上来看,“琵琶”的重逢之用在该剧中都是不应出现的。
综上可见,“琵琶”这一中心道具在《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剧作的故事模式,主题中心的不同,又使得这中心道具的功效,包含的意蕴,表达的情绪,情感的张力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本文作者为田颖,请勿将本文用于商业用途。
相关内容
- 如何避免练习钢琴时的不良习惯 2014-11-24
- 如何防止过度练习产生的伤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对摄像机你该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演奏文凭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9级教材目录2014-11-17
-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考级8级教材目录2014-11-1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