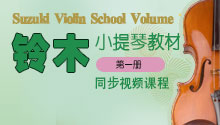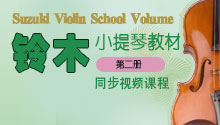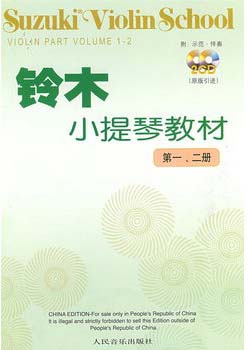在大地上凝视生与死(三)
导语: 2011年5月18日是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逝世10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对这位音乐家致以最深切的怀念。 在中国人眼中,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很难与众所周知的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相提并论,但正如有评论所言:马勒是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乔伊斯和毕加索一样,帮助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他那些将合唱融入交响乐的作品令人沉思。他的交响乐作品规模宏大,长度和乐队的编制部分都是空前的,再加上场外乐队和大规模的合唱队,充分展现了他音乐中的文学与哲理思想。 他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艺术歌曲和交响曲。在他去世后,大部分作品只受到一小部分人的拥趸,一直到许多著名指挥家重新演绎他的作品,将之推广到全世界后,马勒的作品才散发出耀目的光芒。 Ⅰ 三重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1860年7月7日,古斯塔夫·马勒出生在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农业小镇伊格劳,这里种族多样,各国语言及方言充斥着这个小镇的集市。马勒的呱呱坠地,使当时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统治下的奥匈帝国领地又增添了一名犹太子民。 马勒曾有一句著
Ⅲ 《大地之歌》与中国的不解情缘
马勒的《大地之歌》是整个交响音乐文献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融入了一个音乐家对生命、心灵的感悟和寄托,虽然马勒从未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却能够领悟到东方古典诗词中的那种旷达、多变、美丽、哀伤、神秘的元素,并将之通过自己的心绪重新演绎出来。
这部作品是马勒去世前3年(即1908年)所作,这一年,他的长女玛丽亚去世,马勒无意中读到汉斯·贝特格翻译的唐诗集《中国之笛》,他突然大彻大 悟,明白了原来大地才是万物之母,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得归于大地!人源自自然,生来之后立于大地,生老病死、四季循环等现象都是自然的造化。
马勒花了几个星期在同年9月完成了这部作品。《大地之歌》超越了自我保护性的限制与平衡的抒情风格,与陈腐的慰藉或泛神论几乎毫无关联,就像马勒在 1884年,在卡塞尔写的一首诗一样:我在梦中见到了自己可怜的、沉默的一生/一个大胆地从熔炉中逃脱的火星/它必将在宇宙中飘浮,直至消亡。
虽然作曲家本人为这部作品确定的副标题是为男高音、女低音(或男中音)与乐队而作的交响曲,也就是说,它是一部交响曲,但这部由6个乐章组成的曲,实际上是一部歌曲套曲。马勒在这部作品中终于将自己毕生主要运用的两种音乐体裁交响曲和艺术歌曲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部交响曲与中国听众有着血缘般亲密的关系,主要是因为马勒是受中国唐诗的启发而作的。虽然《大地之歌》中引用到的李白、钱起、孟浩然和王维的7首 诗在转译过程中,将原作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将《咏美人》中的采莲蓬的行为翻译成为采荷花并放入兜里,使得意象显得笨拙而古怪,却有不少篇章基本保留了原诗 的内涵。尤其是第6乐章告别,正寄托了他对妻子阿尔玛不能割舍的思念之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曾数次为阿尔玛演奏此乐章。
马勒在1907年夏天读到当时刚刚出版不久的一本翻译成德语的中国古代诗歌集《中国之笛》,奇怪的是,这本《中国之笛》的译者汉斯·贝特格并不懂汉 语,他是在参照了一些法语、英语和德语译本之后,加工、编纂成这本诗集的。其中约80首中国古诗多为唐诗。单从《大地之歌》中的7首来看,贝特格在借助别 人的译本翻译中国诗歌时进行了浪漫化重写。
在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有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被译到西方国家,孔子、孟子的思想理论、《孙子兵法》、《红楼梦》、《水浒 传》等都出现了好多种文字译本,这些译本一般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很多译文并非逐字逐句的介绍,而是如同上世纪初中国译界之王林纾那样的口译笔录,再加 上中国古诗词中很多意境和时境的暗指、寄托和比兴,几经周转,这些诗词早已改头换面。
马勒根据自己内心的需要,选取了能准确表达自己人生感悟的几个篇章。对他而言,中国这片神秘的疆土上,这些关于自然和生命体相融合的诗歌里,必定布 满了玄机和奥妙,而这种对陌生领域的想象和探索正对应了他的自由体音乐的创作理念,也符合他当时的精神需要。东方诗仙与西方音乐家的一次碰撞,成就了一部 经典之作,也是对艺术创作进行极佳诠释和探索无限可能的一部胆略之作。
马勒在《大地之歌》中从中国古诗而不是他更熟悉的欧洲文学中,找到了与自己的心境契合的因素对自然、人生的苦难以及尘世生命的短暂的体悟并产生精神 共鸣,足以显示中国古典诗歌所具有的永恒、普遍的人性内涵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些优美的诗篇跨越了地域、时代和民族的鸿沟,同20世纪壮丽的音乐融为一 体,证明它们确实属于人类心智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当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接近终点时,马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从这些古老的中国诗篇中得到强烈共鸣,尽管这些思想在马勒年轻时代的作品以及诗歌、书信中已有所流露。他在借这些诗篇表达悲观惆怅情愫的同时,亦展现出极度的凄美之境。
关于《大地之歌》,马勒自己曾说:我相信它将是我最个人化的作品。他最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布鲁诺·瓦尔特也在《古斯塔夫·马勒》一书中指出:在《大 地之歌》里,大地在逐渐消逝;他呼吸到了另一种气息,被新的光芒所照耀这是马勒写出的一部完全新颖的作品……每个音符都传递着他的独特声音,每个词,尽管 来自千百年前的古老诗篇,都是他自己的。《大地之歌》是马勒最个人化的内心表白,也是一切最个人化的内心表白。
马勒未能听到《大地之歌》的演出。在他去世6个月后的1911年11月20日,瓦尔特在慕尼黑指挥了这部作品的首演。
文/范典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