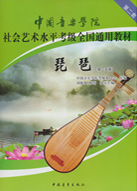嘈嘈切切五十年——王范地和他的琵琶艺术(二)
导语: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王范地的琵琶生涯,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中国人,都在历史的涌浪中载浮载沉,或歌或哭,历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同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摸索、奋斗,有的人用枪杆子,有的人用笔杆子,有的人用斧头,有的人用镰刀,而王范地,用的是琵琶。走过这风风雨雨的五十年,人们回头再看,却忽然发现,虽然大家的方式不同,手段各异,结果也大相径庭,但其为之摸索、奋斗的,却是同一件事情:即为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找一个地位,觅一条出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作为民族音乐家的王范地,在嘈嘈切切的拨弹拢捻中,走过了大半生。 中国的民族音乐,不是没有过辉煌,但那是西周或盛唐的事了。王范地手中的琵琶,也曾在丝绸之路上娓娓地述说过风情,在大唐天子的宫廷里与霓裳羽衣一起制造过诗人的梦境。但到了王范地的少年时代,民族沉沦落后,民族音乐岂能不步履蹒跚、苟延残喘?虽然那时也有过像汪煜庭这样一些在困顿中薪传火种的人,但国破家亡的时代,谁还愿做“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幸运的是,青年王范地还是赶上了好时候,
听王范地青壮年时期的录音,我有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他深厚的传统修养,一是他不倦的创新精神,而这貌似相反,实则相成的两极的统一,则构成了他独特的演奏风格。《春江花月夜》的沉静与优雅,《塞上曲》的韵致与细腻,《霸王卸甲》的阔大、浓郁和强烈、深刻的对比,都让人感到演奏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古典音乐美学的修养。听王范地的演奏,常让人想起“婉约派”的词人,想起柳永的工致谐美,想起李清照的曲折委婉,想起姜白石的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也许是由于他曾演奏、研究过二胡、高胡、京胡等多种拉弦乐器,他的琵琶,在抒情性和歌唱性上显得特别突出。琵琶清脆、劲道、灵动的颗粒状声音,曾被诗人形容成在玉盘上不断跳荡的珠子。但在这经典的诗意联想的另一面,却是琵琶这类弹弦乐器的短处,即与拉弦乐器绵长不断的丝状声音相比,在酿造“韵味”上显得不那么细腻,不那么得心应手。因为颗粒状的声音再细致、再匀密,也不可能像拉弦乐器那样在整个“音过程”中绵绵不绝,如蚕吐丝。“韵味”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它 一是指某种通过乐音表现出来但却超越了音乐形态本身的精神内涵、审美个性以及某种类似“风格”的东西。二是指一种通过音过程体现出来的音高、音色、力度的微妙变化。王范地弹奏的传统琵琶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超越了弹弦乐器的短处,使琵琶的“音过程”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中断”,而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有着像弦乐器一样细腻婉转的细节处理。
在追索传统之外,王范地还在不断地创新。将一切“古老”的东西“现代化”,是一代中国人的梦想,换句话说,上个世纪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试图革新传统,努力以西方文化的视点来审视自己,并努力借鉴西方和现代文化中与我们异质异构的东西。在这方面,王范地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一系列琵琶独奏曲的改编创作,积累了现代琵琶音乐的创作经验,丰富了琵琶艺术的宝库,至今,在沸沸扬扬的“琵琶考级”中,有许多曲目都出自王范地之手。他 1961 年根据电影音乐编创的《红色娘子军随想曲》,第一次以乐器组为琵琶独奏伴奏。他在学习了热瓦甫之后创编的《天山之春》、《送我一支玫瑰花》,使琵琶这件来自西域的乐器“返祖归宗”,重新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封闭的中国人尝到了一点带“异域风情”的音乐。
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讲,舞台生涯的长短常常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但整个艺术生命的长短,却可以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走上教学岗位的王范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作品,精雕细琢,倾尽心血,培养出一批像李景侠、宋飞这样的杰出学生。他在教学方面的成绩,因另有专文论述,这里便不再详述。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晚年致力于民族乐队小型化、多样化的探索,积极扶植“华韵九芳”演奏组,对使民族乐队走出以西洋管弦乐队为蓝本的大乐队模式、回归中国固有的传统,做出了贡献。而回归传统,重新思考年轻时走过的路,不能简单地看成人生的一个圆圈,而的确反映了这一代人从崇新求变到终于发现自己文化定位与传统价值的复杂而深刻的心灵史。
王范地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中国传统艺术家的素养和品质。他不像现代音乐学院培养出的“罐头音乐家”那样只会自己的“专业”,而是擅长多种乐器,能够创作,并重视理论学习,尊重民族音乐学家。这些属于“素养”而被现代教学模式忽略的东西,不但奠定了他“专业”的基础,而且使王范地养成了深思的习惯,使他有可能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提出他的理想和思考。多年前,音乐理论家李凌曾为他写过一篇以他演奏的琵琶曲《飞花点翠》为题目的文章,文中将王范地的演奏比作“清香纯真、饮后犹有余香的好龙井”,以别于“风味浓重的铁观音、红茶和花茶”。我觉得,这个比喻是贴切的。但是,做“龙井”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现代这似乎有无限选择空间并充斥着许许多多“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时候。
①田青 《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8年2期。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