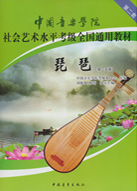嘈嘈切切五十年——王范地和他的琵琶艺术(一)
导语: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王范地的琵琶生涯,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中国人,都在历史的涌浪中载浮载沉,或歌或哭,历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同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摸索、奋斗,有的人用枪杆子,有的人用笔杆子,有的人用斧头,有的人用镰刀,而王范地,用的是琵琶。走过这风风雨雨的五十年,人们回头再看,却忽然发现,虽然大家的方式不同,手段各异,结果也大相径庭,但其为之摸索、奋斗的,却是同一件事情:即为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找一个地位,觅一条出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作为民族音乐家的王范地,在嘈嘈切切的拨弹拢捻中,走过了大半生。 中国的民族音乐,不是没有过辉煌,但那是西周或盛唐的事了。王范地手中的琵琶,也曾在丝绸之路上娓娓地述说过风情,在大唐天子的宫廷里与霓裳羽衣一起制造过诗人的梦境。但到了王范地的少年时代,民族沉沦落后,民族音乐岂能不步履蹒跚、苟延残喘?虽然那时也有过像汪煜庭这样一些在困顿中薪传火种的人,但国破家亡的时代,谁还愿做“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幸运的是,青年王范地还是赶上了好时候,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王范地的琵琶生涯,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中国人,都在历史的涌浪中载浮载沉,或歌或哭,历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同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摸索、奋斗,有的人用枪杆子,有的人用笔杆子,有的人用斧头,有的人用镰刀,而王范地,用的是琵琶。走过这风风雨雨的五十年,人们回头再看,却忽然发现,虽然大家的方式不同,手段各异,结果也大相径庭,但其为之摸索、奋斗的,却是同一件事情:即为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找一个地位,觅一条出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作为民族音乐家的王范地,在嘈嘈切切的拨弹拢捻中,走过了大半生。
中国的民族音乐,不是没有过辉煌,但那是西周或盛唐的事了。王范地手中的琵琶,也曾在丝绸之路上娓娓地述说过风情,在大唐天子的宫廷里与霓裳羽衣一起制造过诗人的梦境。但到了王范地的少年时代,民族沉沦落后,民族音乐岂能不步履蹒跚、苟延残喘?虽然那时也有过像汪煜庭这样一些在困顿中薪传火种的人,但国破家亡的时代,谁还愿做“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幸运的是,青年王范地还是赶上了好时候,他 1952 年以二胡、高胡等民族拉弦乐器考入上海乐团民族乐队,开始了他的专业音乐生涯。本世纪 50 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难忘的青春期、上升期。尤其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充分反映出新政权在政治上的自信和大度,也的确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创造出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以普通劳动者为政治基础的工农政权及其上层建筑的确立,与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文化界、知识界流行的‘波普(大众)文化´思潮同步,使许多过去从未被舆论重视的民间艺术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艺术的殿堂,也使一些在过去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穷困潦倒的民间艺术家有了一个登堂入室的机会。”①而整个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中叶,是风华正茂的王范地的黄金时期,他 1953 年随中国重庆杂技团赴东德、保加利亚、蒙古演出, 1954 年与民族音乐研究所合作进行民族乐器改革的研究, 1956 年随中国艺术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 1956 年改编茅源、刘铁山的《瑶族舞曲》, 1957 年随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参加国际民族乐器比赛并获得金质奖章,同年还随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赴法国巴黎演出,均担任琵琶独奏。 1960 年,他与刘明源合作,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琵琶、胡琴独奏音乐会》, 1961 年编创琵琶独奏曲《红色娘子军随想曲》和《金蛇狂舞》, 1962 年编创琵琶独奏曲《送我一支玫瑰花》和《天山之春》。 1964 年,他调到中国音乐学院担任教学工作,从此基本上告别了舞台,并开始了他作为民族音乐教育家的后半生。
相关内容
- 二胡艺术家舒希 “美丽星期天”开音乐会2014-12-3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