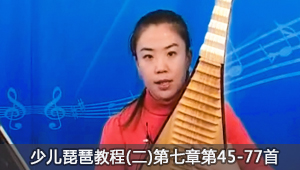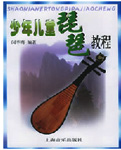坎坷中黄翔鹏揭晓了谜音(二)
大胆推测“一钟双音”
1969年,黄翔鹏被下放到团泊洼干校。在干校种菜,天天干活,然后是政治学习,剩下的时间他就抓紧研究,以至于一年多没有给家人写信。周沉对女儿说:“这人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她让孩子去干校看看。十几岁的黄天来跑到干校,看见父亲为了搞研究,独自住在化肥仓库。浓烈的化肥的气味特别呛,四年下来,黄翔鹏的气管给熏坏了。多年后黄天来说:“干校的化肥味道最终杀害了他。”
1977年,“解放”了的黄翔鹏参加吕骥组织的考察小组为晋陕编钟测音。他们在太原测完音,人家说:“你们用编钟给我们敲个乐曲吧?”“敲什么呢?”“敲《东方红》吧!”
黄翔鹏在编钟上面找,正鼓音(正面敲)缺少一个音,演奏不了《东方红》,他就在侧面敲出了所缺的音。当时他以为是偶然现象,但没想到在陕西、甘肃,他看到两套编钟正鼓有花纹,侧鼓还有一个小花纹。翻起来看,还有撮磨的调音痕迹。敲出来刚好与正鼓的音相差三度,而且具有规律。于是,黄翔鹏就提出了“一钟双音”的看法。
研究员秦序说:“1977年,黄翔鹏完成了关于双音编钟的论文,在不定期音乐刊物《音乐论丛》上只发表了上半篇,编辑部觉得反对的人多,没把握,就给掐掉了。‘一钟双音’没有文献记载,过去都不知道,所以黄翔鹏的大胆推测,确实不容易被学界接受。恰好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家到工地现场一看,双音编钟!而且上面明显标着一钟两音,清清楚楚,一敲很明确;再看里面,调音痕迹也很明确。证明黄翔鹏的猜想完全正确。”
秦序后来写过文章说:“一个推测,很短的时间就被地下发掘的实物证实,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好像老天爷有意让它证明掉。”
音研所中兴 幸亏有他
20世纪80年代,整个学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音乐学,每一个曾强搬苏联模式的学科全部都焕发出了活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入新的时期,音乐研究所也处在转型的关键时刻,新的思路呼之欲出。乔建中说:“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破坏与动荡,从李元庆去世到杨荫浏去世这五年间,音乐研究所真的没有了主心骨。”
在这历史的关节点上,所里的员工和上级主管部门共同选择了黄翔鹏。乔建中评价:“黄翔鹏和杨荫浏一样,不仅有浪漫气质,而且有奉献精神。我觉得黄翔鹏出来主持工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985年3月28日,比杨荫浏小近30岁、比李元庆小近15岁的黄翔鹏,经过正式选举上任了。黄翔鹏以其非凡的才华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完成了音乐研究所在新时期的“整体布局”。乔建中说:“黄先生一方面忠实地继承了杨所长的传统,完全接受了音乐研究所独特的血统和作风;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成为研究所承前启后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黄翔鹏一上任就明确了“开门办所,以资料为中心”这两件事。他把全所的工作集中到“三刊三典”上,“三刊”指的是:《中国音乐学》季刊、《中国音乐年鉴》年刊和《音乐学术信息》双月刊。“三典”则是《中国音乐词典》及其续编、缪天瑞的《音乐百科辞典》和《二十世纪外国音乐词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思路。
然而,对黄翔鹏在每个学科中贯彻“以资料为中心”的思想,不少人私底下存在抵触情绪。1987年,韩锺恩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直接到研究所参加了工作。那时,黄翔鹏担任音乐研究所所长已经两年了,研究所正按照黄翔鹏的指导在走。韩锺恩说:“当时我们很不理解,我们是研究员,怎么变成资料员了?尤其是刚刚出道的人,总想做研究,怎么能去做资料呢?”后来他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成功的研究员,一定是一个对资料极其熟悉的人。所谓资料,不是搜集文字,而是脑子里对这个文章、意图,都要清清楚楚。黄翔鹏的思想具有创新性。“研究所对我的培养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位37公斤的历史巨人
1989年夏天,黄翔鹏留起了胡子。后来,他因肺心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把胡须刮掉,因为胸前蓬乱而长的胡须不利于清洁。黄天来知道父亲蓄须的意义,试探着说:“给你修理一下胡须。”黄翔鹏同意了。黄天来也没有彻底剪掉父亲的胡须,一直到最后,黄翔鹏是留着胡子走的。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