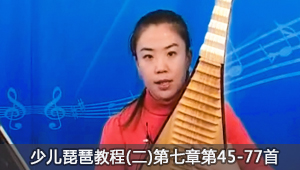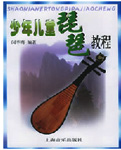坎坷中黄翔鹏揭晓了谜音(三)
黄翔鹏喜欢古琴,琴家成公亮抱着名琴去黄翔鹏家里弹。起先在客厅,后来到卧室,最后一次黄翔鹏吸着氧气听《文王操》。成公亮说:“除乐曲本身的庄严肃穆以外,还有一层莫名而来的悲壮气氛。”
成公亮在《在黄翔鹏先生家弹琴》一文里说: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视角。他把数千年来中国音乐的流传看成是一个活动的、不断变化、不断丰富又不断淘汰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给流传中的中国音乐不断地留下印记。因而,他提出了“传统是一条河流”、“古乐存活于今乐之中”的观念。从这些观念来研究传统音乐,就必须把史学、文献、考古、民族、民俗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这就比狭隘的、孤立的考据更科学、更接近我们悠久的音乐文化历史实际了。
1997年5月8日,不满70岁的黄翔鹏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人生。有人说黄翔鹏是巨人,但在女儿眼里,他晚年瘦得只有37公斤,是37公斤的巨人啊!
一年后,周沉和女儿没有惊动音乐研究所,将黄翔鹏的骨灰送回南京撒入长江。周沉希望陪伴她一起经历了风雨的好人,从长江来,回长江去。
黄翔鹏魂归长江,但是他未完成的《乐问》依旧影响着后来的学者。韩锺恩说:“我觉《乐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残缺的,但是思路绝对顶尖。”
秦序说:“我形容黄先生是音乐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英雄,和命运抗争,就像蜡烛一样燃烧到最后。”
音研所的足迹 学院路·十间房
音研所的前身,是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1953年10月,研究部从天津搬家到北京学院路十间房,一个独立的小院儿里。1954年3月27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
现在一提起十间房,大家很动情。十间房那时在北京算郊区,离城市很远,周围全是农田。没有宿舍,大家都住在办公楼里。二楼办公,住在三楼。吃饭大家都在三楼。后来在院子里盖了三四排的平房,大家从楼里搬到外头去住,但感觉上,还是一个大家庭。
院子里有池塘,池塘里有鱼。办公楼外有两个椭圆形的花坛和篮球场。有一年中秋节,几家人围在一起吃螃蟹赏月,老的小的,其乐无穷。
在新建的四排平房里,顶级学者或专家李元庆、李纯一、李佺民、黄翔鹏、郭乃安、简其华、何芸、文彦、张淑珍……大家都住在一起。
那时候的音研所像世外桃源,同行们都很羡慕。音研所的人权、财权具有相对独立性,领导支配谁,怎样支配,都有主动性。据音乐研究所老人讲,“那时用钱很宽裕,出去买书、买资料、买相机、买录音机,都可以做到。那时候,全国一共几台录音机?录音机进口两台,一台给音乐研究所,另一台给广播电台。那是何等的待遇呀?”而没有那台录音机,现在7000个小时的录音就不可能有。
左家庄·新源里
1967年,音乐研究所搬到了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一号楼。
1982年,乔建中研究生毕业来到新源里工作。据他说,20世纪80年代,同时在这里的有五代学人。第一代是杨荫浏、曹安和、李纯一,第二代是郭乃安、黄翔鹏、许健,第三代是刘东升、吴钊,第四代是乔建中、王宁一、田青等,第五代是张振涛等。
“那个时候,研究所就那么一栋楼,也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老少几代都能随便切磋。不论是谁,办公室的门一敲,就可以进去讨论问题,非常平等地交流。老的,不因为你小对你怎样;小的,对老的更是很尊重。在这样一种非常和谐的环境中,很适合学术的成长。而现在,这种氛围再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乔建中忆道。
有一个时期,音乐研究所高手如云。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博士的论文评价国内几个音乐学术单位,把“音乐研究所”放在第一位。论文作者用了三个参数,第一是人,第二是成果,第三是资料。三者综合,“执起牛耳”的还是“音乐研究所”。
“新源里学派”的“老巢”里,五层楼一个单元,最多时住过二十家研究所的人。虽然缺少京西十间房的豁亮,但是在越来越拥挤的北京能够有一处栖居之地,对于兴趣只在学术的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如今,位于新源里的这座曾经的音研所办公楼,已经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宿舍,其西侧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便是当年音研所研究人员们的住宅楼,现在只有一两位近百岁的音研所老员工住在这里,其他的房子,都已卖掉或出租了。音研所从天津绍兴道4号搬到北京十间房,再搬到新源里,他们住过的地方,在一次次城市改造中已经不见踪迹。这里,几乎成了这个学派集中存在过的唯一建筑实体明证。
图片提供/张春香 刘晓辉 弓宇杰
相关内容
- 汤沐海 每一次音乐会我都酣畅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适合我,坚持走艺术高端路线2014-12-1
- 昆剧名宿林为林:突破自我再现大将军韩信2014-12-1
- 裴艳玲正筹备新戏《渔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现“老普”音乐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学涛的演艺梦2014-11-27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