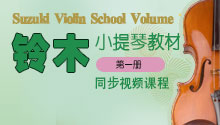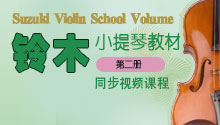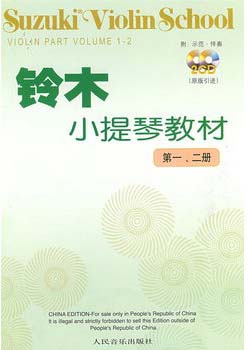麦钧球获斯特拉迪瓦利提琴制作奖(二)
导语:麦钧球展示第13届意大利斯特拉迪瓦利提琴制作大赛优异证书 在番禺大石一个普通的工业区,偏安一处的广州波韵乐器厂并不起眼,不过最近这家工厂却出了位名声大振的人物——麦钧球获得了国际提琴制造界的“奥斯卡奖”。 来自云浮的他有着广东人特有的低调和务实,面对记者的提问,显得局促而紧张,回答也很简洁。被问得急了,他说:“做琴就能做出来,但是讲不出来。” 广州琴师首尝“奥斯卡” 9月27日,第十三届意大利斯特拉迪瓦利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的颁奖现场。麦钧球的师傅曹树堃坐在剧场的三层包厢里,忐忑地等待获奖结果的宣布,这次他带了弟子的6把琴来参赛,赛前徒弟麦钧球的琴呼声很高,曹树堃自信能有所斩获。 公布中提琴第4名名单的时候,现场响起“麦钧球”的声音,旁边的人提醒曹树堃“念到中国人的名字了,你怎么不去领奖?”他匆匆走下楼,可惜的是等到达台前时,已经开始公布其他的获奖名单了,“没有机会现场留影,有些遗憾。” 曹树堃马上打电话给徒弟麦钧球,麦钧球正在自
制作学习过程中,麦钧球觉得弧度最难,弧度对琴的声音有决定性,但弧度也无法用尺子量,只能用心去理解,做出来师傅说不好,自己再琢磨问题出在哪里,下次换另外的做法,经过日积月累的无数次重复,最终“形在心中”。
麦钧球也曾经想过放弃,在做了10年时间之后,似乎仍然闷在原地,没有可喜的成绩,也有些厌倦工作的单调乏味,加上亲戚叫他去做其他更赚钱的生意,他当时有动摇过,师傅曹树堃这时候稳住了他:“做了10年了,你再坚持一下,一定会冒出来的。”
麦钧球听了师傅的话,最终坚持了下来,“他这个人很长情,能做15年很难得的。”一位工友这样评价麦钧球。
参赛回顾
从美国风格转型意大利风格
广东的提琴风格基本走美国风格的路子。国际知名提琴制作大师郑荃曾对广东提琴界倡议,要敢于挑战意大利提琴界,不要光走美国风格的路线。曹树堃也有挑战的想法:“意大利比赛更难,不仅要求琴的工艺好,声音也要好,我们也想试一试。”
100多年树龄的美国枫木
为了做好参赛准备,麦钧球2年前就开始筹备提琴的制作,从选料开始就极为讲究,他的老师曹树堃先生从美国带回来100多年树龄的枫木供他使用。
制作之初就完全按照意大利提琴的老风格来。“比如油漆,我们一直认为红色好看,但是在欧洲看来红色很刺眼。我们以为颜色光亮很好,但是人家认为看起来不舒服,应该柔和,要掌握人家的要求,做出来的琴才能得高分。”
曹树堃让麦钧球停下手头的其他工作,专心做比赛琴。他专门为麦钧球的中提琴设计史氏风格的新样,新样更丰满。曹树堃还重新设计了弧度,让穿透力更好。“取料、拼缝、制作、油漆、装配每一步都要好,一步不好,满盘皆输。”
埋头苦做8个月
这是麦钧球第一次做新样,做新的弧度,又是比赛琴,心里压力很大,埋头做了8个月,每天加班加点。做好之后借给美国的音乐家使用,“让琴的声音保持在那个状态,练琴不是练习拉琴的技艺,是练琴的感觉。琴是有灵性的。很多音乐家拉完这把琴,感觉似乎跟乐曲的作者在对话一样。” 曹树堃说。
为了6把琴坐头等舱
在去意大利参赛时,曹树堃像宝贝一样带着6把琴,不能邮寄、不能托运,怕磕磕碰碰损坏了琴的工艺和声音,曹树堃特地买了头等舱的机票,“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这几把琴。”
曹树堃提前两天到意大利,到达之后在宾馆里马上把空调调到跟广州差不多的温度,让琴适应。他最后一天才去交琴,就是为了让琴最大限度地适应当地的气候。获奖之后,别人开玩笑说:“给琴享受了头等舱,琴就给你拿个奖回来。”
梦想专门给女儿做琴
麦钧球的琴目前还在意大利展览,他并不打算立刻出售这把琴,准备拿回来再研究,再提高。曹树堃也鼓励麦钧球“学无止境,继续提高”,以后继续多多参赛,“没经过比赛就像没打过十八铜人。”
现在麦钧球7岁的女儿也开始学拉小提琴了,爸爸获奖之后,她逢人就说:“我爸爸是做小提琴的。”麦钧球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小提琴家,而自己可以专门给她做琴。
斯特拉迪瓦利大赛
斯特拉迪瓦利大赛是当今世界上水平最高和难度最高专业性最强的一项提琴制作比赛,有“提琴界的奥斯卡奖”之称,要求参赛者必须为专业制琴师,“赛前要把履历报上去,业余的没有资格参加”。该赛因其规格高、专业性强,参赛选手总是一奖难求。该项比赛不分工艺与音色奖,只有按工艺与音色合计总分的高分者才能进入决赛。
而麦钧球获奖的这次比赛有来自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超过500名选手参加,是历来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广州日报 李渊航/文 王维宣/图)
相关内容
- 上海乐展:艺术钢琴夺人眼球2014-10-9
- 上交音乐厅昵称:“馄饨皮” 2014-9-9
-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营销路径2014-9-5
- 乐器企业:上市有甜头 入市需三思2014-8-8
- 曹西岐老人琴上忙活50多年钢琴调律手艺传给两代人2014-7-16
- “艺术哈尔滨”:华夏艺术殿堂的一朵奇葩2014-6-9
热点文章
乐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击膜鸣乐器。又称羊皮鼓。汉称羌铃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