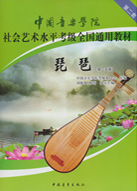秦末虞姬岂能弹奏北朝的琵琶?(二)
导语: 古装电影与历史考证,似乎是一对难解难分的“冤家”。从《英雄》中刺客轻松突入秦王宫廷,到《夜宴》中皇后单身一人出入宫禁;从《赤壁》中曹操无视长江天险派步兵袭击吴军,到《战国》中孙膑未受膑刑之前就被称为“孙膑”,大量与史实严重不符的情节成为古装大片饱受观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票房过亿的《鸿门宴传奇》中,多处违背音乐史的镜头让人啼笑皆非—— □ 假设虞姬真的弹上了琵琶,很明显她是“乐盲”,因为弹此琵琶需要横抱、用拨子弹,而她是竖抱、用手弹。 □ 楚歌是一种歌咏形式,而不是器乐曲。但是《鸿门宴传奇》中“楚歌”的演绎则是用百名将士齐吹横笛的形式。 □ 若此,电影里的虞姬应是“女乐”、“妓女”,但是这种场景是凭空臆造的,想要这事件完整地发生,必须要在宋以后。 □ 编铙在殷商时较为盛行,西周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想到七八百年后,在咸阳的秦宫里还有踪影。 电影《鸿门宴传奇》剧照 让我写下这篇
虞姬“卖艺女”身份辨
在《鸿门宴传奇》中,虞姬一出场就是在男性老板的领导下、与其他几位艺女一起在酒肆里给秦军弹琵琶卖唱,并被责令脱光衣服。称“老板”者,明显是一组织者、领导者。其她几位艺女应是和虞姬一样身份的、同属于一个组织的成员,可能地位会稍比虞姬低些。称之为“卖唱”,虽没有金钱交易等直接的证据,但所有这些关键词关联到一起,不是卖唱也不可能。
“脱光衣服”一节,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对女人的奇耻大辱,更何况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还一直鼓吹妇女的贞节比生命更重要,但虞姬却脱了,虽然有个理由是为了不让秦兵伤及无辜的项羽。其实按照封建道德观,虞姬应该宁愿选择自刎也不脱,或者即便飞蛾扑火也要与秦兵决一死战。更重要的,虞姬想过没有,脱了之后,项羽会怎么看自己呢?但是,虞姬脱了。这一出戏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一,秦兵认为虞姬的地位非常低下,极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否则也不会出这个难题;二、虞姬自己也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脱就脱吧。
所以,总结以上信息,电影《鸿门宴传奇》中虞姬的身份是“卖唱女”。此“卖唱女”在历史上称之为“女乐”,《中国音乐字典》解释“女乐”:指“奴隶社会以来,供统治者阶级享乐的女性乐工”。这是比较雅的称谓,还有“妓女”之称。《后汉书》卷七二《济南安王康传》载有康的儿子错,爱康的“鼓吹妓女宋闰”之事。杨荫浏先生也指出:“在公元100年左右,已有专业的女性鼓吹乐人,称为‘鼓吹妓女’。”若此,电影里的虞姬应是“女乐”、“妓女”(与今之称“妓女”稍有别)无疑,声色娱人、地位卑微,“脱光衣服”居然让电影给演对了。但是,这种场景是凭空臆造的,想要这事件完整地发生,必须要在宋以后。虞姬把自个儿当成李师师了。
首先,这一时期的民间市井尚未出现专门为音乐奴隶生存而设的机构和场所,还没有记载说此时民间有这样演乐的场所。其次,此时专业女乐多作为类似媵妾的音乐奴隶被豢养在各个都城的贵族官僚门庭之中,女乐一般不会在民间走穴。再次,这种以班主为领导的、奔波于各大小酒肆的乐队组织、演出形式,公元20世纪以后多见。最后,“卖唱”的经营方式,需要到宋以后的勾栏瓦舍里才能运作。
三弦、编铙及其他辨
限于篇幅,此段不再引文考据了,直接说结果吧。
还是得再重复那几场戏——虞姬在酒肆里给秦兵卖唱一出:与虞姬同时献艺的还有三位女同事,她们都弹同样的乐器,但是我琢磨了半天都没看出这是啥乐器来,对照音乐辞书,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名称,你看它:弦为三根,脖子长长、音箱大而呈长方形。三根弦的乐器还真不多见,似三弦,但三弦没有这么大的音箱,而且还是长方形,这音箱倒像是马头琴,但是却无马头,于是就姑且称它为“马肚三弦”。
还有刘邦找回虞姬琵琶那一出:在厅堂里摆着诸多琵琶的后面,有一个乐器的背景——编铙,虽然只是背景、画面模糊,但还是能辨别出它的身份来,这次没有费劲,因为形制上不是“四不像”,至少在远处看时是这样。但可惜的是,它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编铙在殷商时较为盛行,西周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说其功能被甬钟所接沿。没想到七八百年后,在咸阳的秦宫里还有踪影,除非秦皇喜收藏。还有,此组编铙共有九枚,这种编列形式很少见,相信看到此影片的考古学者们将会熟记在心:咸阳宫里有九枚的编铙。
综上,本影片中与音乐有关的场景一共就这么寥寥几处,却没有一处、一个细节是符合史实的,杜撰就罢了,却在不经意间改写了中国音乐史。
有人说,电影是艺术,“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不是历史。我认为艺术来源于对真实生活的临摹,没有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对真实生活的感悟,一切都建立在臆想之上的、虚无的东西,只能称之为“术”,不能成为“艺”,抑或叫“伪艺术”。人类的艺术史无不在印证,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艺术,方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无论艺术是真还是伪,至少有一种良知,那就是责任心,除非自个儿创造的“艺术”自个儿欣赏,永不让第二人见到,否则就不能只为了追求自个儿的短暂感官刺激,不能成为过眼云烟,而应该有一种社会导向性、一种责任心。本影片获得高人气、高票房的事实,正反映了它应具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即我应向公众传达什么样的理念?答案就是,传达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但是误导了公众对“鸿门宴”的真实认识。
正如剧中所言“有一种棋局,叫做两败俱输”,影片高票房的背后输掉了历史与艺术——对历史的漠视、对艺术的责任。由此,《鸿门宴传奇》才是一场真正的“鸿门宴”。
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李卫(中国艺术研究院)
相关内容
- 上海乐展:艺术钢琴夺人眼球2014-10-9
- 上交音乐厅昵称:“馄饨皮” 2014-9-9
-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营销路径2014-9-5
- 乐器企业:上市有甜头 入市需三思2014-8-8
- 曹西岐老人琴上忙活50多年钢琴调律手艺传给两代人2014-7-16
- “艺术哈尔滨”:华夏艺术殿堂的一朵奇葩2014-6-9
 名称:中音在线
名称:中音在线